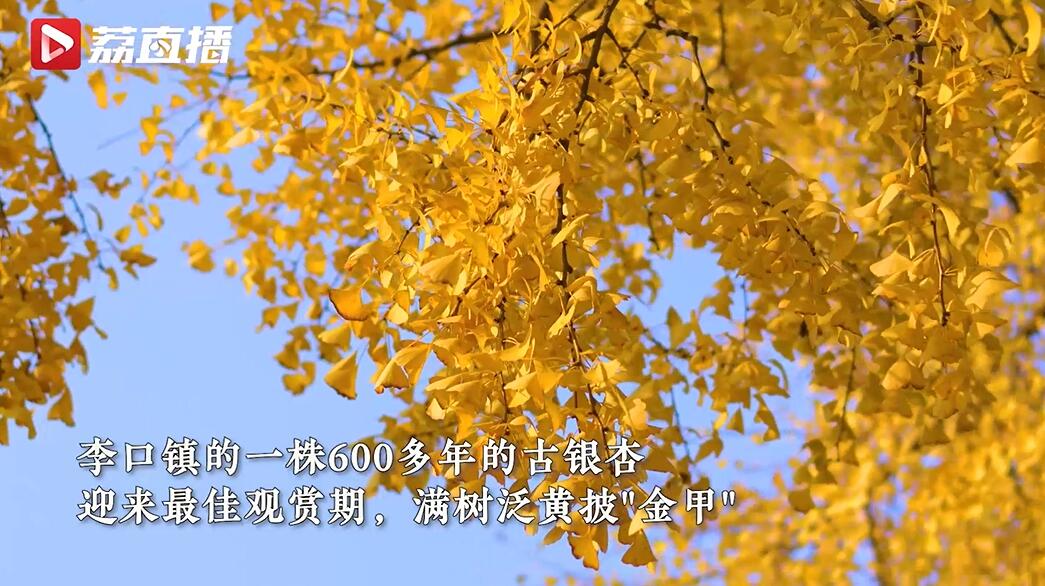2016年12月13日晚7时,来自德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的国际友好人士约150人,200名青少年学生,中日两国僧侣代表以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抗战老兵等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奠广场内,手托红烛、低头默哀,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守灵暨烛光祭活动。 视觉中国供图

2016年12月12日,南京,市民从地铁站的“国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边经过。 视觉中国供图
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关心南京这座城市目前住着多少日本人。兔泽和广是其中之一。
据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小的数字:日本长期排在这座城市外资来源地的前五位;南京是中国的六朝古都,拥有800多万常住人口;300公里之外的上海,则有近5万名日本人。
而南京这个极小的数字还在变动之中,就像是温度计上的读数。每当经济的、政治的气候有一点点变化,数字都会立即作出灵敏的感应。
在过去80年里,“南京”和“日本”同时出现时,通常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符号,代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2017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对于大部分南京人来说,“日本人”的形象既远又近,真实生活中不怎么见到,新闻媒体、历史教科书、电视剧以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则常常耳闻目睹。
实际上,在南京的日本人并不难找。距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5.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聚居区。从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走上18分钟,迈上1700多步,就能跨进他们的世界。
这是石鼓路附近一条小街,分布着各式日本料理店,霓虹灯映出各种颜色的“昭和体”“勘亭流体”文字,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帜。在南京,仅一家点评网站上注册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但真正由日本人开设的只是个位数。没有谁比兔泽和广更加清楚这一点。
他是南京日本人协会的会长,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说得出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话”,被他的中国朋友戏称为“假南京人”。
大约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万人口的南京。多数时候他们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并不起眼。有时他们又是白纸上的几点隐形墨水,在特定的时刻,无比醒目。
兔泽和广亲历过那样的时候。2012年,日本政府引发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很多中国机构和公司突然谢绝和他往来,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为业务开展困难而关门。不过,他并没有打包回家,而是马上又开了新公司。他不打算离开南京。
每年的12月13日,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在这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南京“消失”——“要不在家睡觉,要不就在外地出差”,尽量避免抛头露面。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开始了40多天的屠城。从2014年开始,这一天被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2016年12月13日这天,9时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学日语系学生的试卷。纸张垒成了一个“小山堆”。两分钟后,刺耳的长鸣声响起。
她距离一座容纳这座城市惨痛记忆的纪念馆14公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一个三角洲地带,形状像一把屠刀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区,也指向80年前的那场浩劫,像是无声的长鸣。
听到长鸣,批改试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惊,紧接着脑中一片空白。她才意识到这天是公祭日。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这一天,这位说话小声、一头齐耳卷发、面色有点苍白的母亲,会考虑给学校打个电话,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安慰自己,“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什么”。60秒的长鸣过去,上课铃声又叮叮作响。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入了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因为“超生”,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些年,她感到愈发孤单,和她一样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有的因为婆媳关系而离婚;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两三个熟人。
“‘南京人不喜欢日本人’,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带小孩带妻子过来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宁愿去上海、苏州、无锡工作。”她对记者解释。
2000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时,以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对日本大量战争罪行进行隐瞒。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室与日本民众对话。朱镕基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不过,那时的石川果林无暇关注中日关系。她小时候学过的南京大屠杀只不过是教科书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当时的问题实际而紧迫:作为一个教外国人日语的老师,该去哪个国家教一阵子日语,然后回来找个更好的工作?
在日本学日语的中国人为数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阳。可突然要去的日语学校不办了。她陷入了尴尬:行李打包完毕,房子也已退租,签证也已办好。
当有人问她“要不要来南京”,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正是这个选择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在教书的大学里,她与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师相识、相爱。她的归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诉家里,想在南京结婚,不想回日本。
可父母发了狠话,“不回来就没你这个女儿”,从此再没主动给女儿打过电话,也拒绝到南京看她。
男方家里一样不同意,很多亲戚“呼啦呼啦”地跑过来,分拨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告诫他“日本人当朋友可以,但做夫妻还是算了”。
这对跨国恋人与两个家庭僵持着。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逃过一劫的南京人。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蜷缩在一个凳子上。石川果林对奶奶耳语:“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当时如果奶奶觉得难受,我就打算放弃了,毕竟她见过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国人这么重视家庭。”石川果林对记者解释。
但是,奶奶不带一丝犹豫地回答她:“没关系,没关系。”
“小日本”和“日本人”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台湾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全身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路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他们选择从那家闻名已久的纪念馆开始体会。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看中国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女神”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念馆接待过的外国参观者中,日本人居于首位。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政治和历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3个人和30万人同样需要纪念。”他说,“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发生这种事情。”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民国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人大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北京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他已经打算好:“她愿意结婚,我们就结婚。”
尽管野尻仁通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历史的“小河”,但是水花总有打湿他双脚的时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游行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钓鱼岛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警察。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杀戮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播出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两个中国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媒体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媒体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政治、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打死”。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还手。”他认真地对记者说。
2016年12月13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男子爽快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Nanjing(欢迎来到南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他说,自己不想说话,不想解释。
包袱里的棉花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画作。
馆长张建军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在距离这幅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万人坑”。
“看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过去。”他说。
这位现任的“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把历史问题比作是挂在中日两国民众身上的包袱。“这个包袱平时没有重量感,因为里面装满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时候,这个包袱会变得越来越沉。”
张建军的一本书里夹着一个空信封。封面既没有署名,里面也没有信件。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冈崇光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交给他的。里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学做讲座时的讲课费,捐给了纪念馆。
村冈崇光后来在写给纪念馆的信中说:“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同胞伤害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给我一块钱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如潮的参观者随着那段历史“顺流而下”,年近80岁的村冈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泪,说明词是“请为她拭去眼泪”。村冈崇光在她面前静立了几分钟,拿起手绢轻轻擦拭着塑像的脸庞。
他在信中还写道:“对于我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曾任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先父村冈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驻南京。”
来为先辈赎罪的日本人还有很多。多年前,纪念馆曾经还有一位日本志愿者,也是为父亲而来。
她时常坐在讲解员办公室的拐角上,在一个台灯下默默写字。一本厚厚的记事本上,全都是纪念馆墙上悬挂的讲解词的日文翻译。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状,一头整齐的短发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张“国际志愿者服务证”,小挎包里随身装着记事本。
她视力不佳,在看讲解词的时候,需要尽力将半个身子前倾,脸几乎贴到展板上。那些解说词需要讲解两个小时,她从每一块展板上面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展板上的日语大都是由中国人翻译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叫黑田薰,来自大阪,她在纪念馆附近的宾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平时就在纪念馆里为日本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
周一休馆,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寻找拉贝故居、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等二战遗迹。她不懂中文,但总能碰到给她带路的中国人,有人会送给她胸花作为礼物。
离开后,她在给纪念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还远远不够,但哪怕一点微薄之力,我也要怀着对南京的热爱,在日本不断大声呼吁,不断地将历史传承下去。”
她的父亲,也曾是侵华日军。
这些年,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难以统计。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与任何人交谈。在他们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说日语”。
他们只是默默观看,默默离开。
只有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工作人员,能够从他们的发型和穿着上,发现一些端倪,彼此心照不宣。
对于纪念馆的秘书而言,带日本友好人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
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秘书往往会上前打招呼,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但也碰上过有人控制不住情绪,丢下一句“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故事发生。
馆长张建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铭记那段历史? “1937年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80年,三代人过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时候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纪念馆里走一遍。尽管如此,他说就连自己有时候“心里也会起波动”。
“当前大屠杀纪念馆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当时强调的主题是人类‘浩劫’。10年后,纪念馆主题或许从‘浩劫’转向为‘记忆’。‘浩劫’有一种情绪,罪恶事件本身就能引发一种情绪。但记忆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谈爱国不能再用头脑发热的方式,而是思考怎么团结和自强。”
他说,那些战争的受害者,比如曾经的慰安妇,都是因为国家贫弱,而为国受难。而“尊重、帮助、补偿那些因为国弱而‘吃了苦’‘受了难’‘丢了命’的人,这就是一种铭记。”
在他看来,“砸日本车”“抵制日货”“在网上骂日本人”都不是铭记历史的方式。“真正的铭记是我们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更有素养、在各自领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业绩。”
张建军说这些话时,语调沉重而缓慢。
游过那片水域
每当有新生入学,石川果林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学日语?
以前的学生都会说,是父母让我们学的,方便找工作。现在的学生说得较多的是喜欢动漫,想听懂。
问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有她。不过在她看来,意图却不同:“我的出发点是学习的动力和发展方向,而有人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学这种敌人的语言’。”
当她从日语课堂上走出,就一下子淹没在南京的人潮中。她拥有中国妈妈共同的烦恼:抱怨孩子压力太大,每天都在写作业。“应该像日本的小学生一样,放学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去锻炼身体”;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闹矛盾,把对方给咬了,她拎着水果登门道歉。
只有在上日语课和跟孩子用日语对话时,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质。她的中文阅读有些吃力,辅导孩子做一年级的数学应用题都十分费劲。哪怕题目是“下列哪些是大于10的偶数”,有时她读完一遍也看不懂题目。
三个孩子中,她最担心内向的老二。有一次在饭桌上,石川果林随意问了老二:“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说你妈妈‘小日本’‘日本鬼子’?”儿子的回答是:“只有我们班一个老师常会讲这种话。”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假的?”儿子笑着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愣了一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的肝啊”。
她意识到自己孩子身上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
“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时,我真的无法回答。真相只能自己去寻找。”她说,这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压力。
她希望孩子们以后能够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工作两年,再来思考这些问题。
2017年元旦,兔泽和广回了一趟大阪,这是他来中国24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他感叹大阪没有以前人多,也没有人穿和服“过年”了,不如中国热闹。
他回家看日本的新闻,会格外注意与中国有关的言论。就个人感受而言,他认为自己听到的“中日要搞好关系,亚洲一定要团结”的呼声越来越多。“以后中日肯定会越走越近。”
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发达得像建了一个地下城市,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南京新街口的世贸到中央商城直线距离不过100多米,却要上上下下过地道,打通不就好了吗?”
可过完“年”,3天后他又回到了南京。他说他离不开南京。
“人的存在是因为世界还需要他,而我还在南京,证明这里有人需要我。”在南京,他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总会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为生病需要他推荐医生,因为发生纠纷需要他出面调停,或是因为签证到期半夜打电话求助。
时至今日,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到达南京的日子——1993年3月10日。
坐了一夜火车,他从南京站走出,打量了一眼这个城市:蓝天白云,阳光映射在“金陵明珠”——玄武湖上。
他拿出一张地图,发现目的地在湖的另一头。当时,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用日语在心中自嘲:“难道我要游过去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原载于2017年1月18日)编辑/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