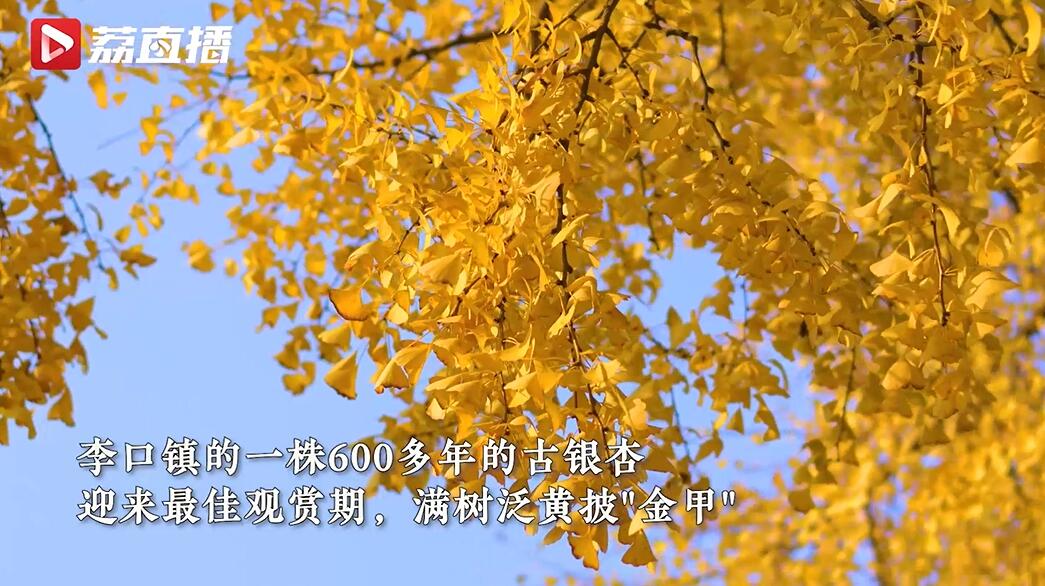浑浊的黄海上,在吕四渔场作业的渔船正在陆续归航。一只只白色的海鸥,盘旋在每艘渔船上空,觊觎着什么。
吕四渔场地近长江出海口,冷、暖、咸、淡不同水系在此汇合,使得这里成为多种名贵水产品的繁殖和摄饵的优良渔场。江苏省今年开始执行严格的伏季休渔制度,加上近年每年放流鱼苗蟹苗,让这个季节成为“十年来最好的开捕季”。
开捕意味着丰收和喜悦。想到又有好多带鱼、小黄鱼等丰腴味美的海鲜捕捞上岸,无数人的味蕾早已被挑逗起来。记者不是贪心的海鸥,仅“代为探看”。

邂逅“苏启渔02377”
去年新修建的吕四渔港,泊满了连日靠港的渔船,人声鼎沸处,是那正在卸货、交易的场所。渔民将一筐筐冷冻好的各色海鲜从船舱中,顺着临时架起的滑道推送上岸,岸边的伙计迅速将它们分类堆放——带鱼、黄鱼、螃蟹、梅子鱼、杂鱼……
一股浓烈的咸腥味,飘荡在空中。
穿着西装拿着账本、边抽烟边招呼过磅的人,应该是收鱼的老板;开着电动三轮车、伸长了脖子看热闹的,是来往送货的打工者……船上船下的人都在忙碌着,除了问“这是什么鱼、这鱼什么价”能有回答外,他们都报以友善的微笑,然后诧异地看着我。
是啊,到渔港,来到正在卸货的渔船前面,不买卖鱼不谈论行情,还能干吗?
听不懂当地方言,别人也没心思回答与买卖无关的问题,记者一个人傻傻地站了会儿,只能决定去别处转转,找其他人聊聊。
苏启渔02377号静静地停泊在岸边,23日靠港卸完海货后,50岁的戴永华与七八位伙伴一直在船上忙碌。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忙着补渔网。
“能聊聊吗?”记者仍然担心打扰他们的工作兴致,惴惴不安地问。
“行啊!你是干吗的?”戴永华抬起头,露出“小马哥式”的微笑,一下子打消了记者的顾虑——有戏。
得知记者的来意,戴永华并不奇怪,因为,吕四渔港经常有记者到访。
“我上船已经20多年了,以前是渔业公司的,现在改制了,我成了打工者。”
“9月15日开捕以来,我已经是第五次下海了。每天挣三四百元……哦,现在捕的带鱼多一点,其他品种不多了。”
“估计这次能卖20多万元,但坏了3张渔网,需要修补。除了人工工资、油钱,船老大估计也挣不到什么钱。”戴永华身上的衣服,还是出海前穿的那套,满身泥浆和油污。
一旁干活的肖建国接过话题:“现在油价涨得太厉害了,6400元一吨,前年每吨只要4600元。我们一个航程12天左右,就需要5吨。光是油价,就是3万多。”
蓝色的渔网,沿着船帮拖到码头上,渔民们边补边往码头上顺。一张渔网,通常有两三百米长,45米宽。说话间,渔民们似乎补好了一张网,肖建国打招呼:“你先歇会儿,我们干完活再和你聊。”

拉网小调
见渔民们纷纷起身,记者只能跳下渔船。他们都很忙,能聊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今天本地人少,要不然可以打个号子给你听了。”肖建国站在船上,抱歉地对记者说。
“号子?”记者心里嘀咕了一下,不知所云。
七八位渔民沿着船帮面对码头站成一排,捞起渔网的“宽面”,将刚刚补好顺放在码头上的渔网,有节奏地重新拉回船上。
没拉几下,肖建国随意哼了几声,船帮另一头的戴永华默契地应和着,另有两位渔民随即也加入了哼唱。声音不大,记者听不清什么歌词,只觉得他们哼得很有节奏,顺着左右手交替拉网,哼唱就有了轻重缓急、高低起伏。
“这就是号子?”记者惊喜地问肖建国,得到他眼神肯定的回答。
听得出来,并不是所有渔民都会哼号子,有几个一直闷声拉着渔网,显然有点跟不上节奏。冷不丁,一位据称来自河南的小伙子,索性喊起了酒令“六个六啊”“七个巧啊”,引来肖建国等人的白眼。
毕竟不是号子,小伙子的酒令跟不上拉网的节奏,只能悻悻地不喊了。三四个吕四本地渔民,依然轻声地哼着,号子的节奏和手上拉网的节奏,浑然一体。
不知不觉,横铺在码头的那一堆渔网,被重新拉回渔船。对话重新开始。
“你们的号子有词吗?”
“没词。怎么开心就怎么喊,喊得比唱得还好听。”肖建国得意地说。
戴永华说:“启东渔民号子登上过央视星光大道呢……”
“哼号子有什么作用吗?”记者不解地问。
“减轻压力,把郁闷抒发出来……”戴永华依旧憨憨地笑着。古铜色的脸庞,仿佛罗马角斗士,只是多了疲倦,少了张力。

渔民为何不愿“赴宴”?
每个人都在忙,记者只能抽空问上几句。肖建国与戴永华等人,总是尽量满足记者的采访。
“海上捕鱼苦不苦?”
“俗话说,‘撑船打铁磨豆腐’是最苦最累的活,‘撑船’本来就排第一苦。现在打铁和磨豆腐都有机器代替人工了,但捕鱼还得靠我们渔民。”肖建国说。
“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潮来了、鱼来了,就是我们最苦的时候。经常会几天几夜不睡觉,有时候48小时只能睡1个小时,吃两顿饭。”
“海上有闲的时候吗?”
“有啊,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忙,闲的时候,也是整天睡觉。但是,到海上睡觉干吗呢?到海上就是去捕鱼的。我们不忙,老板就要破产了。”戴永华笑着说。
“最危险的时候呢?”
“遇到台风时,船从浪峰到浪谷时,根本看不到船的影子,只有浪头。”肖建国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习惯了,不怕,还得干活。”17岁就到海上谋生的他,经历了太多的风浪。
船老大名叫肖庙如,16岁就随渔船下海,今年56岁了。1996年,他有了自己的木船,当起了船老大。2014年,他个人贷款造了目前这艘200多吨的铁船。“至今也没赚到什么钱,养活了一帮兄弟,还有130万贷款要还。老渔民了,只会捕鱼。”
总算等到船老大空闲的时候,他同样很热情。“前几个航程,都能捕到四五十万元的海鲜,这次不行了,天冷了,鱼也少了。”
“肖师傅,能不能请你们晚上一起吃饭聊聊?”
“今天就算了吧,下次我们请你。”肖庙如也有点为难。
“下次就难说了,我来一趟不容易……”记者仍想努力。
“他们今天才上岸,十多天了,还没回家……”肖庙如的解释,一下子让记者的邀请,显得多么“不知趣”——远征回来,家人的团聚当然更重要了。
“留个电话,下次随时欢迎你过来,不忙的时候,我们好好聊。”戴永华也终于得到了解脱,因为船老大帮他们妥善地拒绝了邀请。
“忙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谈不上,最起码,我们各自撑起了一个小家庭,我们的孩子不用再吃这个苦了。”戴永华的回答,永远是那么实在。

悲鸣之音
离开码头,记者来到吕四镇的富华水产品冷冻加工厂。这里不像渔港那么繁忙,起码能找到人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富华水产品冷冻加工厂副总经理朱金华,正将双腿翘在办公桌上看手机。
“今年幸亏封海(伏季休渔制度)抓得好,让我们渔民有饭吃,我们的子孙有饭吃,菜篮子也有饭吃。”朱金华激动地说,“我们起码要比往年多赚三分之一”。
52岁的朱金华,只在25岁到28岁时上过船,但因海上工作太累,且风险太大,至今没再下过海。“人一掉海里,就没了。”朱金华说,那时候下海的都是木船,保障水平也很低,尽管现在都换了200多吨的铁船,他依然对大海心存敬畏。
前不久,吕四渔港北边的小洋口港,一条渔船海上作业时与大船相撞,落水13人,只救上来11个人。
正因为海上作业既累又苦风险大,跑船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在岸上上班每天200元,海上每天400元,但年轻人还是不愿意去。现在的渔民,多在50岁以上,还有很多65岁的老渔民。”
朱金华所说,与记者在吕四渔港的观察完全吻合。“渔民在岸上是人,在海上像鬼啊!”一位陌生的老汉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我年轻时也上过一次船,上去以后就一直躺着,躺了十多天,吃什么吐什么。什么都不敢吃,就只能躺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上过船。”
记者曾经幻想着和渔民一起体验海上捕鱼生活,像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一样能“笑傲江湖”,感受那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激情,却在这种“只能躺着,不能站着;只能喝水,不能吃饭”的现实描述面前,选择放弃,尽管戴永华等人一直热情邀请。
海明威之所以能写出《老人与海》这样的名作,曹雪芹之所以能留下《红楼梦》这样的传世名著,都离不开生活经历和磨难。日本的《拉网小调》之所以成为世界名曲,那同样是万千北海道渔民呕心沥血、搏击风浪的吟唱。
海上的艰辛,记者这辈子是没法体会了,也没法就此写出更生动更激情洋溢的文章。就像南方人无法体会北方的天寒地冻,北方人难以理解南方的酷暑炎热,异乡人的情怀,总是融不进当地人的血脉,无法真正触摸他们的痛苦和快乐。
有幸听到戴永华等人哼的原汁原味的吕四“拉网小调”,让记者更近距离地触摸他们的生活。努力想象着他们在海上用小调排遣郁闷、提升与风浪搏击的勇气,似乎还有点浪漫的意味在。但陌生老汉说“渔民在岸上是人,在海上像鬼!”的这句话,一下子将记者拉回到现实中来,恍然大悟!
幸福的人,通常都是默默无闻的。因有愤懑,所以摇滚。因为有了苦难,所以渔民才哼唱出了“拉网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