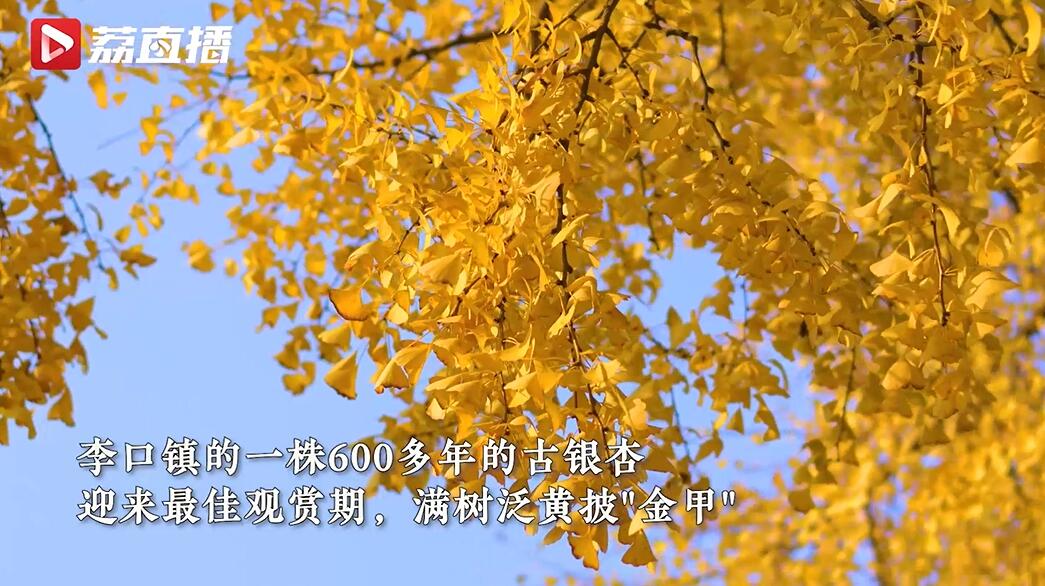文/周俊生
(作者周俊生,荔枝新闻特约评论员,资深媒体人;本文系荔枝网及旗下“荔枝新闻”客户端、我苏网及旗下“我苏客户端”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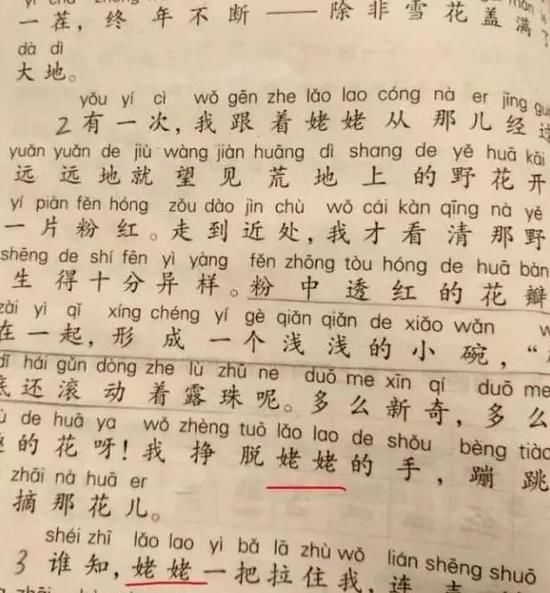
上海自编的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一篇题为《打碗碗花》的文章,因为编者将其中出现的“外婆”一词全都改为“姥姥”,最近两天引起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其实,这个问题在前两年已经引起过疑问,只是未引起舆论关注,在此次的热议中,上海市教委在一年前的答复也被挖了出来,其中关于“姥姥”属于普通话词汇而“外婆”为方言词汇的说法,更引起了舆论的一致声讨。

上海市教委的这个答复,牵涉到很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对于“外婆”一词是否属于方言用词,这两天已经有多篇文章出现,压倒性的意见认为它的使用范围比“姥姥”广泛得多,因此,如果一定要剔除教材中的方言用词,“姥姥”倒是一个更合适的目标。
也许是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昨天上海市教委要求教材出版单位上海教育出版社在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核查,并作出答复。出版社表示,修改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但这个理由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难道非要用这篇课文来学习“姥”字吗?
而“外婆”是方言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目前国人使用最多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外婆”和“外公”确实被标注为方言用词,而“姥姥”“姥爷”这两个词则未有这样的标注。在词典面前,很多论者就气短了,困为在很多人看来,词典是具有权威性的。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词典?词典作为一种工具书,在我们的学习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现代汉语词典》,由于发行量巨大,已经成为汉语学习和使用的重要工具,取得了权威性的地位。但是,只要是词典,它就是由人编写的,而只要是由人来完成操作的,就难免会出现错误。事实上,国内有不少语言学家都对这本词典提出过意见,如果我们有机会阅读到中国辞书学会的会刊《辞书研究》,就会经常看到语言学家对它在选词、注音、释义等各方面存在问题的批评。正因为此,《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在修改,这种修改除了及时收录新词以外,还包括删除一些已经不太用到的旧词,特别是订正一些有问题的词目。遗憾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从1960年编出第一版试用本开始,到2016年已经出版第7版,但各个版本一直把“外婆”和“外公”认定为方言用词。更遗憾的是,尽管几十年来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批评一直存在,但这个明显的错误却未有专家指出,直到此次因为一本教材的修改才将问题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本以普通话词汇为收录对象的中型工具书,对方言用词的收录是很谨慎的,原则上只有已经进入普通话词汇、方言区之外的其他读者也经常能接触到的词,才能够进入这本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本以普通话词汇为收录对象的工具书,对一些词标注为方言,充其量只是交代了它的语源,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功能并不吻合,而且常常会出现挂一漏万的错误,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的士”一词,源于香港,先进入了与其毗邻的广东,从语源上说是一个粤方言词,但这本词典却未将其标注为方言用词。
《现代汉语词典》将“外婆”“外公”认定为方言用词,从这个选择中还可以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而形成,这个标准的设立是合理的,由于北方方言几乎覆盖了中国黄河以北的所有地区,这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但在客观上,它也造成了其他方言的被削弱。少量方言用词可以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进入普通话,但更多的方言用词却会因此而被屏蔽掉。《现代汉语词典》之所以会将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外婆”“外公”认定为方言用词,不能排除是受到了这种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这对方言也会产生影响。以上海来说,现在有大量“新上海人”出现,他们对亲属的称呼自然会带进上海,并且潜移默化地改变上海的方言。此次暴露的是“外婆”与“姥姥”的纠葛,其实,在更早的上海,对父亲的母亲和父亲,是称为“好婆”“好公”的,但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北方人的大量进入,现在基本上已经被“奶奶”“爷爷”代替,“好婆”“好公”的称呼在市区已经绝迹,只有在郊区才能偶尔听到,而《现代汉语词典》则干脆不再收录这两个词了。但就“外婆”“外公”这种称呼来说,在上海乃至整个南方地区仍有广泛的使用,并且也被北方地区人所熟悉,词典将其认定为方言用词是很鲁莽的。这两个词将来是否会被“姥姥”“姥爷”取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口的流动状况,而不是词典。
此次出现的“外婆”与“姥姥”之争,看似一场“象牙塔里的学术之争”,但牵涉的方面却很多,值得相关方面认真思考。这次讨论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不仅对于小学语文教学能够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对待方言,对于正确认识词典作用都有帮助,对于词典的编写,也能产生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