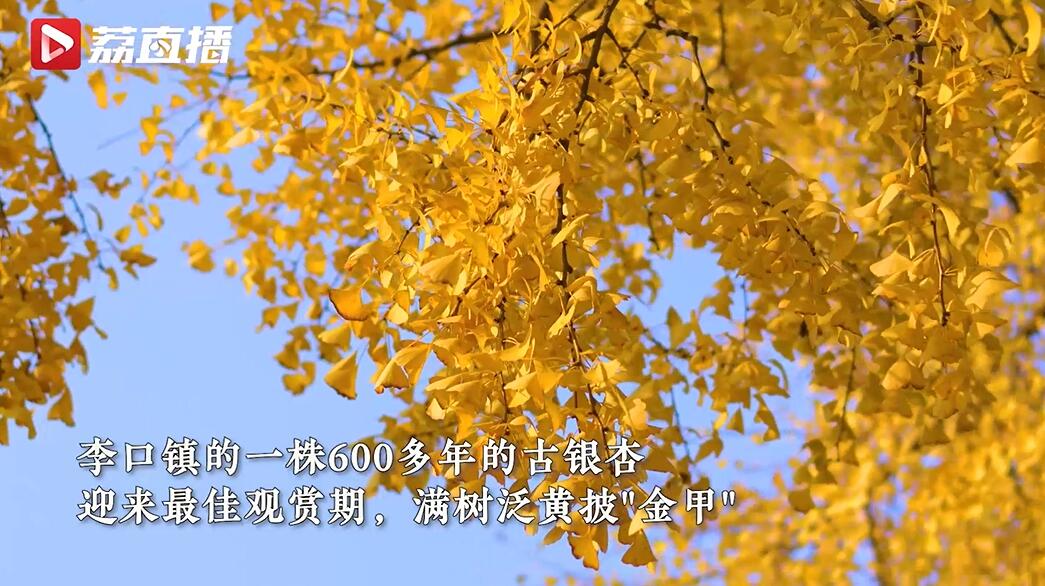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及七七年级入校40周年
序
每每提及回忆性文章,总是难免有“选择性遗忘”或是“选择性记忆”之嫌,无论有意或无意都使得回忆文章的真实性受到质疑。除了记事失真,回忆文章的另一大弊病就是作者的自我美化和升华,使得人物变得俗化或神化。因而我对写回忆文章总是有点望而生畏。
西班牙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巨著《百年孤独》中说过“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过去都是假的,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无法像做科学研究那样去考证每一个回忆的细节,然而回忆也並不都是消极的,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多数的回忆中有历史和人性。
人们都说七七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从进校前到入学后,从在校时到毕业至今,每个人都有那不能忘却的蹉跎岁月。在过去的28年里,我一直从事专业的眼库工作,並且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就试图致力于中国的眼库建设和发展,这个鲜为人知的工作在七七级出国的同学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七七级入学40周年之际,确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二十多年在眼库方面的工作和生活经历。面对手边的数百封各种信件和不同的年度报告,还有千百张照片,我试图理顺自己的思绪,记录历史的真实。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客观真实地记录我所经历的国内外眼库的发展历程以及自己在此过程中走过的坎坷道路,从而给自己和其他感兴趣的人以一定的反思与感悟。
入库不虞
与大多数八、九十年代满怀抱负或是希望改变生活而出国的人们不同,我的出国却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目的—探亲。
我和先生黄一飞都是南京医科大学(原南京医学院)医学专业七七级学生,1982年毕业后留校,我分配在南医一附院眼科,而一飞则分在一附院胸心外科。黄一飞于1988年在读研究生期间由南京医学院选送、国家教委公派到澳大利亚 (Australia) 阿德莱德(Adelaide) 攻读博士研究生。他走时我刚刚怀孕2个月並且正处在自己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和毕业分配的关键时刻。
从1988年4月黄一飞赴澳至1990年3月我去探亲的两年中,我独自经历了完成硕士研究生论文、通过论文答辩的全过程,以及毕业找工作的挣扎,生子的痛苦,养子的艰辛和申请出国探亲的不易。这其中离不开家人的鼎力支持和同学、同事以及一飞和我的研究生导师的关心与大力帮助。是家人的亲情、师生情和同学情深深温暖着我的心,使我两年中不再感到孤独。
1989年下半年,在黄一飞出国一年半后,根据一飞出国时所签合同,我向学校申请自费出国探亲,但是我没有料到的是学校只批准我一个人出国,儿子得留在国内,理由是教委规定中只有“配偶可以探亲”並无提及子女。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顿时傻了眼。这个决定无疑就是逼着我要么要丈夫,要么要儿子。走,不满周岁的娇儿托付谁人?留,牵肠挂肚的丈夫何时能见?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的家人站了出来。为了让我们能够夫妻团聚,为了让我安心出国,已是南京体育学院教育学副教授的母亲毅然放弃了晋升正教授的机会,申请提前退休为我带孩子,那时候母亲才56岁(注1:当时高校高级职称的退休年龄为60岁),对于她那种五十年代中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且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这样的决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牺牲。正因为此,当初当我踏上澳洲土地时,我並无丝毫兴奋之情,而且也从未想过会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国。
我是1990年3月8日离开上海经香港转机赴澳的,3月9日抵达阿徳莱德。在香港转机时闹的笑话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次到香港机场,有近三个小时转机时间,于是便在机场的商店中转悠。当时身上只有刚按国家规定兑换的600澳元,计划作为我下三个月在澳洲的生活费。(注2: 当时出国可以按国家外汇牌价用人民币兑换500美元,再按美元对澳元的牌价把美元换成澳元。500美元换到了610澳元,这在当时国内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出了国门,还不够一般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为囊中羞涩,只好做橱窗购物。但是很多商品确实很吸引人。我在卖化妆品的柜台上看中了一套修甲工具,产自日本,小巧精致,要价约15澳元。店员看我素颜,在卖修甲工具的同时又极力向我推销口红。出国前我父亲给我买了一支眉笔和一个粉盒。因为父亲不知道我要什么颜色的口红,他让我自己去买。可是因为走前太忙,心境也不好,最终没买。这时经店员的蛊惑,我想我确实需要一只口红!因此就选了一支最便宜的兰蔻。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支口红。那时的香港机场免税店收多种货币,一般按港币的价格换算后收取其它币种,但是不收人民币,所以只能用澳元支付,算下来这支口红约合25澳元。当时的香港机场免税店营业员少有会国语的,大多数人除了广东话流利外,英语和日语口语也带很重口音,而我不会广东话,英语听说也很差,勉强听懂了要付多少钱,我拿出一张刚换的崭新100澳元,店员说沒有澳元找,只能找港币,我只好同意。可是要命的是我此前从来没见过港币长什么样!因为是买免税品,她要了我的登机牌。正当我还在为自己的奢侈感到负罪时,店员惊叫一声说我的飞机已经登机了。她塞还给我登机牌和一堆钱以及装有我买的东西的购物袋,叫我赶紧去登机。香港的机场真的很大,我根本找不到要去的登机口。看看手表,飞机还有十几分钟就要起飞了。情急之下看到对面走来一位机场保安,赶紧向他求救。同样语言交流有极大障碍,我把登机牌给他看,他终于明白了。这位先生非常给力,他立即用对讲机与登机口联系,然后接过我的旅行袋让我跟他走。我们走了十来分钟,路上我听到广播里用英语叫我的名字,他把我直接送到机舱口,飞机还在等我!(注3:那时的安检很简单,因为有保安送,我们走了工作人员快速通道)。到了澳洲后我拿出从香港机场找回的“港币”,才发现其中一张最大面值100的纸币是摩洛哥国的货币,我晕!口红、修甲工具和那张纸币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是那个年代我们傻冒和无知的见证。想想当时机场的店员看我一定比王熙凤看刘姥姥还不屑。现在香港回归了,港人国语也流利了,今年在香港机场免税店购物,感觉店员对我比刘姥姥对贾母还恭敬。
阿德莱德是一座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是澳大利亚南澳州的首府和商业文化中心,人口逾130万。城市非常整洁美丽且清净,特别适合做学问。我和一飞租了靠海边一栋别墅中的一间。一飞每天早出晚归去城里大学做试验,我除了做点简单饭菜就是学英语,晚饭后我们去海滩上散会儿步。日子看似悠闲,可是我非常想念在中国的孩子和亲人,英语几乎是一点也学不进。一飞看我整日神魂颠倒,孤影独游,怕我憋出病来,于是就想给我找点事情。在他的导师推荐下,我递交了生平第一份简历。由于我有硕士学位,经过简单面试后,我来到了福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 眼科系做访问学者,认识了我眼库生涯中的第一个“贵人” Professor Douglas Coster 以及他的分管研究的助手Dr Keryn Williams。
Flinders大学于1966年建校,是以英国探险家马修•福林徳斯 (Matthew Flindrs)命名,以纪念他探索南澳海岸之功绩,学校离市区10公里。该校的生物技术,医学和环境科学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而以角膜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著称的眼科系是该校的领军系科。
Coster教授是澳大利亚眼库的先驱。他于1981年在福林德斯大学医学中心成立了澳大利亚的第一个眼库。1985年,Coster和Willisms教授创建了澳大利亚角膜移植资料注册中心。这是国际上最早建立的有关角膜移植和眼库质量控制的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角膜移植资料库。
刚去眼科时,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和听力不够好,Coster教授就安排我在实验室协助他的一个博士生做棘阿米巴角膜感染眼病的研究,眼库就在实验室的一隅。那时国内的角膜移植手术刚刚起步,显微手术几乎尚未开始。南医一附院仅卞春及, 谢丽娜主任等少数医生能做,后袁南荣主任从日本回国后推广了这项手术,我给他们当过助手。苦于供体材料的匮乏,一年仅一两次机会而已。我们的角膜材料都是从供体身上直接取了移植给病人。作为小医生,我们参与角膜移植的最大任务就是从尸体上获取眼球送到手术室。我从没有听说过眼库,更不知道做角膜移植必须要有眼库作保证。
到南澳眼库工作后,我第一次知道眼库是获取、鉴定、处理、保存和分配捐献者眼材料的机构。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捐献者的需要並把安全、优质的角膜材料按受捐者的需求分配给角膜医生用于手术。眼库实验室的技术主要包括材料的鉴定、制备以及保存。我对眼库技术感到很新奇。
由于有了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我的英语口语进步很快,两个月后Coster教授允许我跟他去临床看病人和学习角膜移植手术。我向他提出想学习眼库技术,他和Keryn都很支持。此后我便在不影响实验和临床工作的情况下跟眼库的工作人员学习眼库技术,並且独自开始了一个与眼库有关的研究课题--角膜保存。我本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课题,但是因为1989年“事件,1990-1991年度澳大利亚的国家奖学金停发给中国学生。虽然此时我有研究助理的工资,但是也支付不起学费。幸运的是1991年我申请到澳大利亚大学妇女联合会的一份为期一年的资助,得以先行开始课题研究。1992年澳洲国家奖学金重新开放后,我以这个课题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申请到1993年始读的为期三年半的澳大利亚国际研究生奖学金(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
我的事业看似顺利,但是生活却并不平静。当我开始了Flinders大学访问学者工作后,为工作方便,我们搬入大学医学中心单身护士宿舍居住。我们租了两间宿舍,一间做卧室,把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另一间做起居室、书房和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是楼层里共用的。记得我刚到澳洲时,黄一飞只有一只带缺口的碗,一只平底炒锅,一只小的煮饭锅,一把小刀,一个砧板和几双筷子。菜是用筷子炒的,作料仅有油盐和胡椒粉,当年这个用筷子炒菜的习惯我一直延续至今。当时一飞的全部生活费每月只有380澳元,由国家教委发放。除去房租、电费和交通费后,所剩无几。物质生活的贫乏倒能对付,思乡的折磨却难以忍受。自从来澳洲后,我和一飞一直想把儿子带到身边,但是总不能如愿。那时候办护照需要单位证明,可是我们费尽心思却怎么都得不到一纸公文。为了排遣思念,我把自己的工资都贡献给了澳洲电话局。当时澳大利亚打中国的长途是3.5澳元一分钟,我每周都会打1-2次。为了便于通话,专门给母亲家安装了直拨电话。每次听着电话那头娇儿的声声呼唤和母亲的嘤嘤啜泣,我也是肝肠寸断。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1993年3月,儿子终于得以与我们团聚。当年离别时他只有14个月,如今已经是4岁有余,但是因为分别太久,儿子的心中只有外婆、外公和小姨。在过去的三年中,是我的父母和妹妹代替了我们尽了本该我们应尽的责任。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对小小的他则是困难重重。我和一飞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儿子建立起正常关系。由于我不能在南澳州读书,而一飞又无法在昆州工作,一家人面临才相见又分离的境况,我也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选择:要么放弃课题和奖学金留在阿德莱德一家团圆,要么忍受再次分居去昆省读博。其实在国外的中国学生,夫妻各自为了事业分居两地的比比皆是,可是我对分居两地实在恐惧。现在儿子刚来,如果一家人再分开,我们和儿子的正常关系更不容易建立。于是我毅然决定放弃读博的机会,留下相夫教子。所幸的是,在关键时刻,黄一飞的导师,世界著名麻醉疼痛大咖Michael Cousins教授施以了援手。他证实了我的国家奖学金作为学费可以带到澳洲的任何学校,只是大学发放的生活奖学金需要放弃。Cousins教授正好拿到悉尼大学麻醉科教授职位和一笔可观的研究经费,他需要黄一飞帮助他在悉尼皇家北岸医院(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建立动物实验室。于是他帮我联系了悉尼大学临床眼科和眼卫生系 (Discipline of Clinical Ophthalmology and Eye Health)读博,如此我们一家得以搬到悉尼生活,我也因此认识了我眼库生涯中的第二位“贵人”Professor Frank Billson。
转库艰辛
1993年晩秋,我们一家搬到悉尼(Sydney)。(注4:澳洲地处南半球,与中国季节相反,秋季是3-5月)悉尼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是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 State)的首府,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最稠密的城市。悉尼城市也是欧洲首个澳洲殖民聚落以及罪犯的流放地,1788年由英国第一舰队的船长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ip)首建。现在悉尼是澳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国际主要旅游胜地,以海滩、歌剧院和港湾大桥等闻名。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1850年,是全澳洲历史最悠久、享誉全球的著名学府。悉尼大学临床眼科及眼卫生系创建于1964年,首任系主任是Frank Claffy医生. Frank Billson 教授于1977年接任第三任系主任,並于1985年创建了下属研究机构“拯救视力研究所” (Save Sight Institute)。Billson 教授是著名的小儿眼科专家,在澳大利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享有盛誉。他是第一任西太平洋区国际防盲组织主席和前联合国亚太地区防盲主席。为了防盲治盲,他的足迹遍及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中国,新加坡和新巴布几内亚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我的另一位导师Dr Penfold是位形态组织学和免疫学家。
悉尼大学眼科以视网膜病,眼发育和小儿眼科研究著称。1993年时科里没有角膜病研究和眼库。无奈我只好重新选择“眼和视网膜血管发育”作为博士课题。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博士生导师时,Professor Billson 瘦小精干,西装革履; Dr Penfold高大魁梧,牛仔T恤,一对典型的澳洲医生和科学家的标准造型。
初到悉尼,首先遇到的生活问题就是安家。悉尼地广人稠,但却不识一个说中文的朋友。黄一飞在皇家北岸医院工作,而我则在市区眼科医院读博。我们先在一飞医院的旅馆里暂住了两周,最终找了一个离医院较近的单元房栖身。以前在阿德莱德租的都是带家具的房子,现在悉尼的房子里除了炉子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重新置办。我们全家打地铺三周才得以有床而卧。
接下来的问题是儿子的入托。孩子已经4岁半,需要上幼儿园。可是一飞医院幼儿园一周只有三天有空位,剩下两天始终不着落。最后在Billson教授太太的帮助下,我在离眼科医院两站路的悉尼著名红灯区Kings Cross找到一家幼儿园可以提供剩下的两天服务。可怜的孩子每天清早7点钟出门,跟我坐火车去幼儿园。幼儿园规定每天下午6:00前必须要接,否则每过时一分钟罚款10澳元。因为我的实验常常要做到晩上8-9点才能结束,所以我每天下午6点先把孩子接到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给他买点吃食,让孩子在我办公室待到我实验结束再一起回家,这常常已是晚上9点以后。孩子精疲力尽,多半在火车上就睡着了。这么折腾的结果就是他经常生病。每次他生病,我和一飞只好轮流看护他,白天一飞上班我带孩子,等一飞下午5-6点下班后,我去医院做实验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回家。睡3-4小时起来再看孩子和做家务。
转学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我失去了大学的生活奖学金,加上悉尼突然增加的托儿和生活开支,我们常常是入不敷出。为了生活我每周还要去一座办公楼做一天清洁工。那时候清洁工的工资每小时10澳元不需交税,干一天可以挣到80澳元,这对我们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1995年Billson 教授受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之命接管了州眼库。当时眼库建制不全,效率极低,不能满足新南威尔士州角膜移植的需求,非急诊病人常常要等待2-3年才能做到手术。Billson教授知道我在南澳眼库工作过,就让我参与眼库重建和实验室工作。当时因为我还是全职学生,只能工作部分时间。就这样我又重新回到眼库並成为新南威尔士州眼库重建后实验室里最早的科学家之一。1998年当我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我面临再次选择:做全职眼库工作,或是在大学做全职视网膜病学术研究。由于我实在舍不得丢掉其中任何一项,于是折中的选择了各50%。
自1995年至今的23年中,新南威尔士州眼库从原来全澳洲效率最低的眼库发展为今天全澳洲最大的眼库。角膜移植从1996年每年442例到目前按需获取,每年约800例左右,捐赠和手术量占全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捐献和手术总量的38%,等待手术病人从1995年一千多人,到现在完全按需取材。此外眼库还引进了新的角膜保存和材料预制备技术,拓宽了其它诸如羊膜,巩膜等材料的供给,开展了诸多课题研究,至2018年,眼库已经发展成为了新南威尔士州组织库(New South Wales Tissue Bank), 提供骨,关节,皮肤,心脏瓣膜等移植材料并成立了澳大利亚眼生物库(Australia Ocular Biobank),为科研提供眼组织材料。我们确实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
眼库实验室虽然不用去供体取材,但是仍需要7天24小时工作,随时处理捐献的材料。实验室只有一个半人,我和同事轮流值班,一年每人要值180多天班,直到2018年初,实验室才增加了一个编制。22年中我把4000多个日日夜夜包括节假日都献给了捐赠者和受赠者,这其中也离不开一飞和儿子的通力支持。记得2010年的新年除夕轮到我值班,晚上悉尼海港及大桥燃放焰火戒严,但是正好有人捐献,我需要去医院处理材料。当时汽车和火车都不通了,一飞陪我步行一个多小时穿过悉尼大桥赶到医院处理材料直到第二天清晨。澳洲的新年正值盛夏,我们被来自于自然空气和庆祝除夕快乐人群的热浪包围着,走到医院时,我们衣衫湿透,大汗淋漓。那一年我们做了最早用工作迎接新年的人。那夜的个人收获是我在大桥边拍了一张特别好的焰花照片,做成了2010年的贺年卡。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其实眼库只是我的50%工作,我还有视网膜、眼底病的教学与科研。我深知没有家人的扶持,我走不到今天。
建库无怠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眼科医生开始走出国门,学习国外新的技术。我的导师Billson教授是天津眼科医院袁佳琴教授的朋友,而Penfold博士则与广州中山医眼科的吴乐正和吴德正兄妹有过合作,因此我们那里常有中国眼科医生来访。Billson教授是推动中澳眼库合作的始驱动力。1997年我在悉尼与Billson教授一起接待了中国的眼库先驱,中国眼科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山东青岛眼科研究所的谢立信教授,他也是我眼库生涯中的第三个“贵人”。
在谢教授来访期间,他表达了想建眼库的愿望,谢教授已有丰富的眼库经验,从美国回国后谢教授建立了青岛眼库。1998年,我第一次到青岛访问,带去悉尼眼库的操作程序並就中国现代眼库建设与谢教授进行了探讨。当时正值寒冬腊月,我从烈日炎炎的澳洲回到北风呼啸的中国,穿的是向妹妹借的棉衣,从南京乘火车去青岛。本来我的回程车票是第二天下午的,但是当天下午忽然下起大雪。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谢教授预计第二天很有可能火车会停开。当时年关将近,改票或再买票绝无可能,于是谢教授立刻找到他认识的青岛火车站的站长,得知傍晚有过路车去南京。谢教授把我送到火车站,拜托站长把我送上火车,站长又托了这趟车的列车长(遗憾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那时从青岛到南京火车要十多个小时。我在火车要开时被塞上一节硬座车厢。因为是无票乘车,受托的列车长安排我先待在列车员休息车(又叫宿营车)。领我的一位年轻列车员小吴姑娘告诉我一直往后走,到列车员车厢等她。硬座车厢里拥挤不堪,真的是寸步难移。我花了二十多分钟才穿过一节车厢,幸好我没有行李而且只要穿过两节硬座车厢就到了硬卧车厢。硬卧车厢乘务员问我要票,我只好搬出列车长来。她们看我也不像流串人员,就把我从硬卧车厢送到列车员休息车。记得列车员休息车是在硬卧的最后一节车厢。车厢里有如硬卧车的铺位,但是上面都睡了人。车厢近车门的地方有一块稍宽的空间,堆了很多行李。在车厢壁上有两张並排的可自动弾回的小折椅(又叫边凳),是给上铺的人临时坐了穿鞋用的。我就在一张边凳上坐下了,过了一会,小吴来了,她告诉我今晩可能都不会有空铺。虽然车厢里有暖气,但是寒风从车厢连接处的门下钻进来,直吹到靠近门口的座椅上,冰冷刺骨。半夜里列车长来打了个招呼,很快又走了,我都没有看清他的脸,感觉他很是辛苦。列车员是轮流占用床位休息的,那些睡在床上不起来的人显然不是工作人员。我就这样在边凳上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到达南京。回家后我就病倒了,那次病后,我失去了部分嗅觉。次年谢教授在青岛组织了第一次全国眼表疾病和眼库研讨会,我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狮子会会长Ron Reavly应邀参加並做技术培训,说起那次坐火车的经历彼此感慨颇多。当时参加那次眼库培训班的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是国内各眼库的领导。此后至今,我和谢立信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谢教授始终鼓励我为中国眼库建设出力,并为我在国内眼库交流提供帮助。
我在国内第二个工作过的眼库是地处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眼库。早在1997年西南医院眼科主任阴正勤教授在悉尼做完博士后回国前夕和我商量过建立眼库之事。在Billson教授的支持下,于1998到1999年间,我参与了西南医院眼库的设计和建设。西南医院眼库于1999年正式成立。此后我受聘为三军大客座教授和眼库顾问共十年,几乎每年都去那里做培训和带学生。除了眼库以外,我为西南医院眼科医生在悉尼眼科医院进修搭建了桥梁。西南医院眼科先后有5位医生在悉尼眼科医院和Save Sight Institute访问和进修学习,我在悉尼的家也成了这些进修医生的大本营,他们回国后大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想想那时候去西南医院,也就是住在医院招待所里,每天服务员送两次开水,每天供热水2小时洗澡,但是我常常因为忙,错过供水时间,弄得几天洗不成澡。我是在三军大食堂里第一次吃到东北名菜酸菜猪肉炖粉条的,在解放碑的好吃街上吃的第一碗担担面,在街边的小店中享受“巴适”地道的重庆火锅。(注5: “巴适”是重庆方言“好吃”的意思)
自1993年开始从事眼库工作后,我一直很想为南医一附院眼科做些什么。起初我每次回国都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一些角膜移植的手术器械和角膜保存液。那时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一分为二,卞春及和袁南荣主任各领导一方。因为袁主任是角膜医生,所以我带回的东西主要提供给他,有时也给卞主任领导的眼一科。2008年时我帮助袁志兰主任建立了江苏省眼库,但因种种原因眼库并未很好开展工作。虽然我从2008年起正式受聘为南医大眼科的客座教授,其间帮助联系过人员来澳进修,但是和眼科的合作主要在科研方面,直至2018年起开始帮助刘庆淮和袁松涛主任重建眼库和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药物试验。
除了以上这些眼库外,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先后帮助过济南,深圳,厦门,成都,南京(南京市红十字会眼库),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的眼库建设和人员培训,大部分的访问都是自掏腰包。2010年,悉尼大学专门为我做了个眼库交流短片在上海世博会上播放,悉尼大学的专刋上写有重庆三军大西南医院眼库和江苏省人民医院眼库的信息。2017年作为第二主编,经过历时5年收集整理资料,我与国内同仁们合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眼库技术专著《现代眼库实用技术》,谢立信教授为此书作序,该书2018年出第二版。我自费购买了100本书送给需要的眼库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这本书尚有很多不足,但是希望它多少能给中国眼库工作者提供一个规范化的基本操作指导。目前我正在撰写由孙旭光教授主持策划的眼表疾病系列丛书之一《眼库规范化操作和管理》,
希望进一步给基层眼库工作者以简明实用的指导,也能为中国眼库采用国际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
兴库有望
近年来随着角膜移植手术的不断更新,国际眼库技术也飞速发展。澳洲的眼库己经从以往个体的单一采集、鉴定、处理和分配角膜的材料库发展为器官组织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开展了合作性工业化材料制备流程,服务于新型的移植手术。
中国有400万角膜盲,其中200万患者在等待角膜移植手术,而每年全国所能做的手术只有5千例左右,角膜材料一多半购自海外,(注6:2017年1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要求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境外来源的人体血液(包括血浆及其他血液成分)、组织器官用于临床医疗用途,目前中国角膜材料全部来源于捐献),眼库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很多眼库有库无眼。角膜病患者大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急需救助。
2016年我随黄一飞回他老家盐城农村,我发现他的一个堂侄,一位20多岁的俊小伙子,一只眼睛因为几年前受伤感染形成角膜白斑,白斑正在瞳孔区。我初步检查后认为是很好的角膜移植适应症。当我告诉他手术可以治疗他的眼睛时,他说曾去盐城医院看过,医生说没有角膜材料,而且手术很贵。“反正你有一只好眼,这只眼就随它去吧”!医生如是说。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了,我真的感到无语和无奈......
随着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日益增长,在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角膜移植手术已日益成为角膜病治疗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中国的眼库遍地开花,全国已有75家眼库,数目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一些地区积极创建眼库联盟,开展区域性合作,提高捐赠率和材料使用率。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捐赠的重要性。在中国眼库和角膜移植的领军人物中活跃着我们南医七七级同学的身影。我相信有他们的引领和辈出的新人,中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建立更多的与世界接轨,集取材、鉴定、保存、预切一体化的新型眼库。自己虽为凡偶近器,夕阳黄昏,但仍希望继续为中国眼库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虽然马尔克斯认为记忆中的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是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但我以为那些日子的重现正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有过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不在乎过去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在乎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而现在仍然还在或已经不在我们生活中的人。岁月不居,故人萦梦。经过40年的生活沉淀,每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七七级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对人生的反思和感悟,我们不可否认七七级人属于那个时代。
苦难铸我坚强,真爱塑我柔肠。我感恩过去,珍惜现今!
2017年11月29日
写于悉尼
2019年2月10日
修改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