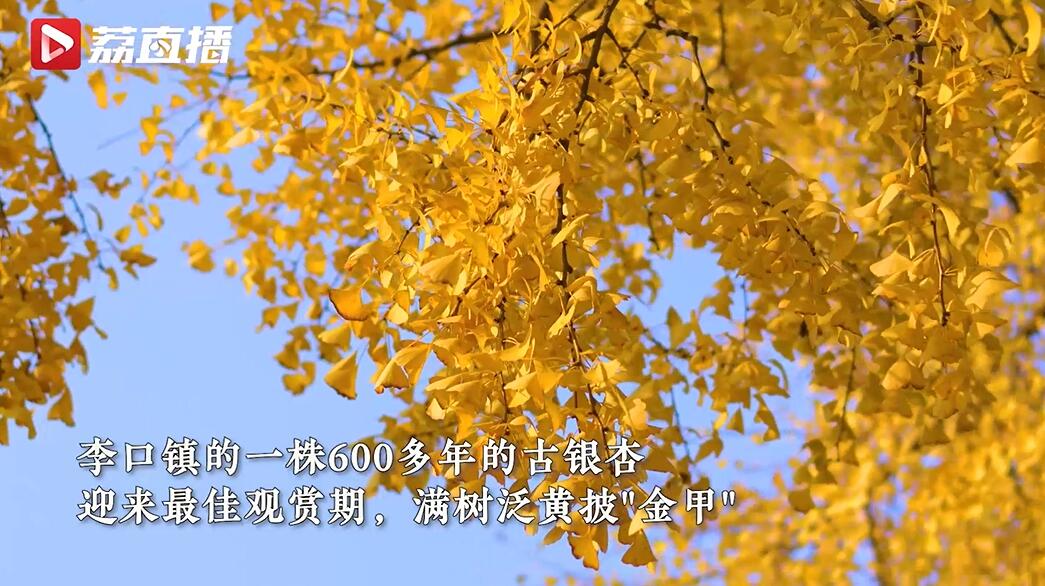涓滴成海 岁月有光
回眸凝望 山高水长
与你一起留住时光 重温南师校史
感受百廿南师的精神气脉
读懂南师人的品格与魅力
中大楼是一个三面开门的古典建筑,坐落在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随园老校区的西山山麓,建成于1956年,为一倚坡而起的富有传统特色和魅力的T型建筑,处于随园校区传统宫殿式建筑群的中轴线上。
爱上中大楼的理由有许多。爱中文所以爱中大楼,是诸多理由中的第一理由。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我作为江苏省中学生作文大赛的一名决赛选手,第一次走进这栋中西合璧风格的大楼。我怀着无限的崇敬,甚至掺杂了些许卑怯,仰望着参天的大树,合抱着、掩映着她的沧桑姿容。我拾着数十台阶而上,从北门走进了一间阶梯教室,在这里写出在大赛中夺魁的散文《门》。从东门走出去,有一片草地,花草繁茂。我嗅着不知名的花香,沉醉而又少年得志。当我眯缝着眼睛,抬头透过花丛望去时,影影绰绰之中,一块不起眼的小红匾牌,悬挂在门头:中文系。

丁捷在中文系读书的年代,大学生流行军大衣
呵,中大楼,一直是这所百廿学府的中文系所在地,这里会聚着时代执守的人文梦想,吴贻芳、陈鹤琴、高觉敷、唐圭璋、孙望、吴调公、吴奔星、徐复……这些走进人文史的大师,在这栋建筑里进进出出。青砖黑瓦、红柱黄墙、飞檐翘脊、曲径回廊、高台厚基、层梯错阶。它呈现着曲折婉约的仪态、古色古香的风韵;它更有突破传统的四通八达、面相开远的明朗气象。分布在过道两侧的教室,吟唐诵宋,说东道西,谈古论今,指点江山。光阴荏苒,日月煌煌,弹指一瞬啊。记得在中大楼求学的日子,有一天听完一堂唐诗欣赏课,被诗仙李白的华丽文采打动,激动的心情不能平静。是什么天力赋予十几个世纪之前的诗人如此神奇的才华?汉语艺术的巅峰,为何由他创造,千年万千文人骚客竟然无法超越?是什么样的水土里,升腾出这般巨星,其光辉一直闪耀于浩瀚时空,成就人类文明的不朽?
四川,他是我们四川人!一位四川籍的同学,高声地陈述着:“四川江油啊!古书上多有记载的。”
古人也是考据推测,这个我不认同。另一位同学大声驳斥道:“我更倾向于郭沫若先生所论证的‘碎叶’!”
那也太“外国”了吧!四川同学不服地说:“那是遥远的中亚腹地啊!是哈萨克斯坦,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啊?”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从感情上,我似乎更愿意相信,伟大的诗人李白出生在很西很西的地方。我说,大唐的疆域,东到黄海,西及咸海,北至西伯利亚啊!李白的出生地再西、再西一些,也不会是“外国人”啊!
在中大楼的过道里,我与一群同学言辞慷慨,辩论激昂。这时,一位身穿灰色布衣、个子不高却很硬朗的先生过来插话。“碎叶,郭沫若先生所说的碎叶,即便没有那么精确,但至少为我们指示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答案。”他说,“我认为,李白出生在现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附近,你们回去翻翻地图,记住了,翻世界地图。”先生说完,严肃地冲我们点点头,就转身走了。
先生就是国内权威的李白研究专家、古文献学教授郁贤皓先生。他用了大半辈子心血和智慧,把李白浩瀚如海的诗歌著述、深远莫测的身世游历,以年表的形式,准确地整理罗列出来。最后,这些资料为他相对准确地推断出,李白的出生地,就在当时隶属中国疆土的美丽的巴尔喀什湖流域。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轰动了文学界和史学界,也引起了又一轮李白出生地的考据争论热。

丁捷大学时代热爱文学和书法,八人一间的宿舍是丰富的文艺场
曾经在许多个夜晚,我独自坐在中大楼的台阶上,望着斑斓的星空,遥想西域,心潮起伏:李白出生在巴尔喀什湖流域?李白出生在巴尔喀什湖流域!是啊,我们伟大的文学先人李白,出生在那么遥远的西域吗?在那浩荡的丝绸之路,祖先的足迹一直向西绵延,望不到尽头,诗人踯躅而行,渐行渐近,走到了我的跟前,想释去我们的狐疑……可千百年来,我们数代学人,皓首穷经,企图弄清楚这样的学术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丁捷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在西山九舍简陋的宿舍里建立小家庭,那时候简单就是幸福
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一位老画家家里,欣赏他的私藏书画。有一幅林散之先生的书法,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西望瑶池”, 林老的四个字,营造出沧桑、邈远而浪漫的意蕴。我久久地研读这四个字。我记得这是李白的好友诗圣杜甫诗句里的一句话:“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那一天,老画家跟我一直在谈论这幅作品,谈论“西望瑶池”和林老书写这句话的可能用意。老画家说,他看过好几件林老含有瑶池内容的书法作品,也听林老说过自己对瑶池的理解,中国古人所说瑶池为西王母的降生地,隐含一种东方文化里的西部情结,因为不能从海上向东行,只能通过大陆西进,去追寻一片圣池。瑶池是一种归宿吧。往虚处说,代表东方的梦想,代表生命旅程的目的地,它是美好的,遥远的,难以到达的!但是,在大唐及后来的数个朝代,瑶池虽远,但国力可及。而到了清末和近代,几纸条约,使它成为更加遥远的异国他乡。老画家说起这些,音容沉郁。他觉得林老就是在抒写这种憋屈的情结。

丁捷的获奖摄影作品《与我同行》取材于新疆赛里木湖,用镜头描画了梦中的瑶池
我沉思片刻,问老画家道:往实处说呢,瑶池,有这样一个地方吗?
老画家夹着纸烟,使劲儿吸了两口,然后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目光炯炯地望着我,说:“我理解,是新疆的某个水域,比如,以杜甫对李白的膜拜,杜甫完全可能把李白的出生地幻化为瑶池,也就是巴尔喀什湖。哈,这当然是我的胡思乱想!”
我的心中像划过一道光,真的,一道光,在那个烟雾缭绕的画家斗室,林老的字,李白的出生地,杜甫的诗句,画家自谓的胡思乱想,那一刻真的合成为一道光,从我的心空中划过。从此,我特别喜欢书写这四个字。每当我闲暇练习书法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写“西望瑶池”。此后的多少年,我自己无法记清,我写了多少遍“西望瑶池”。

丁捷创作的水墨画《西望瑶池》
李白的出生地是不是巴尔喀什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这样的答案。瑶池是不是巴尔喀什湖,我们当然无法确定,但我们愿意相信它宁可是正确的答案。人生会遇到无数为什么,需要无数的答案。有的答案,是在书本上谋求得到的。有的答案,来自智者的解惑。而有些答案,不是一言可尽、不是有章可循的。有的需要用情感去指示,甚至用人生、用生命去解题。我就是在疑惑之中,有意无意地让自己的人生,走近了一个不寻常的答案。
2000年夏天,我迎来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向西远行的机会。当时我在省委工作,得幸参加省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新疆,并看望远离家乡、在那里任职的二十多位江苏援疆干部。在飞机上,我的耳压升高,热血上涌,说不清楚是高空反应,还是心情激动使然,抑或两个原因都存在。我一路听着省长介绍江苏与新疆的渊源,介绍江苏对口援疆的那片土地,叫作伊犁,其有着“塞上江南”的美誉。而伊犁地名,来自祖国唯一一条向西流淌的国际河流伊犁河。我的脑海中立即出现一部文学著作的名字——《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哦,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暗合啊。在我十几岁爱上文学的懵懂岁月,父亲送给我他的几本藏书,其中就有一本王蒙先生的《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这本薄薄的小书,记载了一个热血的作家、青年干部奔赴边疆、融入民族生活的生动经历。这样的生活,甚至传奇般的青春,曾勾起我对未来、对人生之路浪漫的遐想。

丁捷在伊犁清水湾《王蒙文学创作中心》前留影
进入伊犁的上空,飞机上一片惊呼。隔着窗口俯瞰,一束金色的丝带,缠绕在西域大地上。那么飘逸,那么散漫,那么洒脱,那么华丽。这就是伊犁河。我在惊叹声中拿起行李中的小相机,随手拍了一张夕阳中的金色伊犁河。这张照片后来竟然成为一件人人叫好的摄影作品,在多家媒体发表。也许,在兴奋之中,才会有激情的创作灵感。即使是没有任何技巧的创作,也会因才情而赋予作品以神奇。
是夜,我们住在长满百年老树的伊犁宾馆。在伊犁已经工作了几年的援疆干部陈斌先生,也是一位文艺爱好者。他跟我畅谈了一个晚上关于文学,关于伊犁,关于林则徐、张之洞的伊犁事业与诗文,关于王蒙的十六年边陲人生与散文。我送他出门时,透过树林的缝隙,看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陈斌非常突兀地伸出双臂,对着天空和树林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说,啊呀,我们也应该谈谈历史,这个宾馆所在地,就是前苏联的“大使馆”,而原属伊犁的三分之二伊犁河流域国土,正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被沙俄割走的。
那夜,真的很深了。我们没有继续讨论这片土地的历史。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它们,如今是哈萨克斯坦,是吉尔吉斯斯坦,是两个友邻。
后来,我竟然真的成了伊犁人。可能,在第一次的访问中,在无数次的文学阅读中,我的才情已经率先融入了西部,融入了这条河流。中文为我后来的人生,不知不觉缔结了许多缘分。我预料到的、没有预料到的,被人生不断地迎合着、证实着、实施着。

丁捷在伊犁任职期间,与各民族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2005年春天,我与我当年在中大楼里的同门师兄弟曙海聊天,我说我想写一本关于西部情缘的书。曙海曾经援藏三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练达气质。当他听完我的写作计划后,摇头了。
他说,仅仅有这些,说白了,是一点文学和他人情感里的伊犁,过于单薄!
他说,你的人生有多厚,你就有可能写出多厚的书。
那一夜我失眠了。大概两个月后,我看到了组织上的援疆动员令。我几乎没有深思熟虑,甚至没有跟老母亲和妻儿打一声招呼,就写了一份援疆申请报告。我说,作为一名年富力强的干部,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到祖国边疆去工作锻炼几年;作为一名作家,我想把自己人生的一段才情,赋予边疆,抒写伊犁。
这年夏天,我被组织选派,从江苏外派到新疆工作。在我到达伊犁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就来到伊犁河畔。北疆的母亲河伊犁河,带着祖国天山的雪融水,奔腾向西,一直流到了巴尔喀什湖。这条伟大的河流,造就了祖国西部壮阔的绿洲和她哺育出的源远流长的文明。但是,看到这条西域母亲河,她越是美丽丰满,你越是不能不在心里痛惜一个事实:如今她只有三分之一在祖国境内,另外三分之二则在哈萨克斯坦境内。造成此种事实的是腐朽的清政府,1860年和1864年,沙俄利用军事和外交恐吓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据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西部领土,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包裹着一大半伊犁河,从祖国划了出去。
没有人站在中哈交界的地方,心情可以平静。就连同一只在枯树上站立的乌鸦,在我的眼里,也是有些许郁闷的。
这个星期天,我站在伊犁河畔。背倚祖国,望着河流冲积出的一马平川,感慨万千。如果李白的后人,通过郁教授的研究成果,弄清自己血脉的源头,想在清明的时候,去祭奠先人,他们需要履行一大堆麻烦的出境手续。他们站在这里,一定会黯然神伤。

丁捷与新疆各民族儿童在一起
2008年6月,我随同伊犁商贸代表团赴哈萨克斯坦,参加中亚经贸国际洽谈会,有幸驱车顺流去哈萨克斯坦境内。车子过境后,伊犁河变得更加壮阔汹涌。几十公里大漠戈壁过后,河水的滔滔,把流域浇灌得一片葱茏。难怪有人说,伊犁河所到之处,一片西域锦绣江南。我为祖国西域母亲河强大的生命哺育能力感到骄傲,同时更有几分嫉妒,几分失落和伤心。
从阿拉木图飞往哈萨克斯坦新首都的途中,同行的外贸局的李援友提醒我,我们会经过巴尔喀什湖的上空。当飞机上的中国人发出惊叹声,纷纷把眼睛贴在窗口,向哈萨克斯坦壮阔的大地俯视的时候,一片如同仙境、飘浮着薄雾的碧蓝,静静地舒展在万米之下。她的四周,是苍茫的绿郁。
哦,伟大的李白,将汉语推向人类文明巅峰的仙人,仿佛依然就在这片碧蓝、这片绿郁之中穿行。一路向东,一路向东啊,他洒下的诗句,散发着粼粼金光,照亮古国的千年文明,而且不朽。
今天,我们是否敢问,谁是李白的后人?是我们这些读唐诗长大,持着出访护照进入他故乡“碎叶”的现代中国人吗?
那一刻,我真的热泪滚滚。

抒写新疆情感的纪实散文书《约定》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小时候牙牙学语,就从读李白的诗开始。父亲是这样,爷爷说,爷爷的爷爷都是这样;我这样,站在我身边的维吾尔族干部库尔班江也是这样长大的。在王蒙20世纪60年代被下放的伊宁县巴彦岱民族乡,我去看望民族小学的孩子们,他们表演的节目,就是朗读李白的诗歌。在汉语言文学里长大,谁又不是李白的后人呢!
我们的感伤,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

《约定》新书发布现场
在中大楼里,我们的文学带给我们的,究竟有多大意义,已经没有用语言去陈述的必要。
如今,在这座飞檐峭壁的中国古典建筑里,楼道的十字路口,屹立着鲁迅先生的塑像。它是我的校友、著名雕塑家吴为山,送给母校的一份厚礼。楼外的树绿了又枯,枯了又绿。背对这座古式建筑,又有几尊新塑造的教授雕像站在那里。他们是培养过郁贤皓先生的一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古典文学大师孙望、语言学大师徐复。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鲁迅先生锋芒毕露的姿势,构成了中国文学追求真理的多维形态。他们的精神和骨头,并没有不同。他们传承和给予我们的中文血脉,来自同一颗心脏。从李白和他更先的先人,从鲁迅到他更后的后生,无论他们在哪一片土地上奔走,呐喊,他们都同经同脉,同源同生。他们所有的理想和创造,都诞生在祖国这样一个襁褓。
没有中文的洗礼、大师精神的传承,以及对祖国西域特殊历史和地理的见证,没有站在奔腾向外的伊犁河河畔的那些酸楚、那些隐痛的亲身体会,有哪一位在校学子能像我这样,从中大楼的这座鲁迅雕像身上,体会到更多的精神内涵呢?
鲁迅先生有一个刚毅的额头,一代一代的中文系学子,走近他,一定会放慢脚步。当我们稚拙的目光与先生的深炯相遇时,我们感到了民族力量通过中文进行的一种传达。我们也感到了中文的力量,可以在任何方言的土地上,催生统一、向上的精神。

丁捷携代表作、长篇小说《依偎》走进央视新闻联播
在遥远的新疆,从20世纪30年代起,鲁迅、茅盾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就在各民族人民之间广泛传播。维吾尔族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托乎提·巴克,一生致力于推介鲁迅等大师的作品,其丰硕的文学翻译成果和带来的广泛社会影响, 都说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在社会中独特的声音和风范,他们坚定的信念,都具有超越民族、地域的共性,鲁迅激活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心理深层的精神积淀,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创造彼此坦诚对话、共同促进知识繁荣和人类精神发展的话语空间。文学的鲁迅是属于全中国的,每一个民族中的鲁迅都是对鲁迅整体精神的不同诠释,都在使这种精神趋于完善,最终成为能够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正如新疆学者姑丽娜尔·吾甫力所说,鲁迅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品格的代表,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这也进一步证明,虽然民族不同、生活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血脉是相通的。
越过鲁迅的肩头,我们的目光所及之处会更为博大和邈远。

丁捷的长篇纪实文学《追问》一度引领了中国反腐文学热,被称为“现象级”作品
中大楼,三个门分别通向三组台阶、三个方向。走向北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是祖国大后方;走向东边,是紫金山,是远方的海,是海里操着汉语演化的假名的岛国,那个曾经在这里屠城的邻邦;走向南边,当然还是海洋,海洋里有操着汉语的邻居,以及一个被强行分隔的祖国孩子。
有一阵子,我忽然发觉,中大楼唯独没有建筑西门。走上前仔细看,中大楼又是有西门的,只是从来没有打开过。心想,你们为什么独独封闭了向西的门呢?是精心,还是无意?每次,当我经过中大楼,或者想起我在那里进出了七八年的时光,我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惑。它强化了我的思维指向。一堵西门,能不能挡住我们翘首西域,能不能忽略我们瞭望西方?!
当我作为一名长着毛茸茸胡须的蹁跹少年,就读在这栋大楼的时候,也许当年,我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和依恋她。当我把自己的青春和才华融入西域之后,我对中大楼的感情和理解,逐渐改变。每次回到南京和援疆归来后每次经过母校的大门,我都不由自主地走进校园,走进西山山麓的中大楼。楼,有时候长久失修,风吹雨蚀,陈旧斑驳,有时候又焕然一新。树木还是那些树木,只是更苍劲和高大;台阶还是那些台阶,只是更厚重和坚实。学生时代的许多老教授早已离世,与我们在楼道上讨论李白出生地的郁贤皓教授也已经满头白发,更多年轻的学子,穿行在吴为山先生创作的塑像中,穿行在老而不朽的中国文学经典的字里行间。

丁捷和同学们每隔几年就组织一次返校活动,在中大楼的教室里坐一坐,重温青春,感慨万分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我特意来到随园,登上中文系大楼的台阶,踏着满地黄叶,怅然自顾地拾级而上。那已经是我援疆凯旋几年之后的事了。我走到台阶的最高处,差点跟一位先生撞个满怀。抬头一看,是我当年的文学导师何教授。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住,望着对方,有好一会儿,才彼此冲着对方笑了。我说:“先生好,我路过,想起中大楼,非常想念,就进来看看。”先生伸过一只拳,擂擂我的肩膀,说,先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很好啊。
那一刻,我再次热泪盈眶。

丁捷认为,大学如诗,从随园、从中大楼走出去的一代代学子,都会有人生的远方,也都会经常回归这片神奇的学府天堂

丁捷近影
作者介绍:丁捷,当代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副会长。1990年代初期丁捷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在校长办公室工作5年,此后调江苏省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机关、地方党委和国企集团的副处级秘书、宣传部副部长、纪委书记。丁捷在文学上少年成名,当年由南师大免试录取,此后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其代表作《依偎》获得国际、国内七项文学大奖,《追问》长踞全国图书畅销榜文学十强和非虚构榜第一位。他曾当选中国新闻出版年度记忆作家、新浪年度最具影响力江苏作家、当当年度畅销小说作家以及“江苏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专题人物等。
( 编辑/顾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