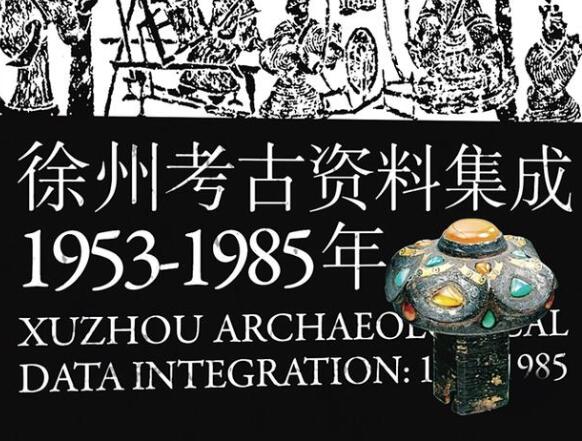28万字、600余幅图表、600余页的《徐州考古资料集成:1953-1985年》沉甸甸地放在案头。这部被列入徐州博物馆创建国家一级馆科研资助项目、收录了59篇考古简报的大书,终于在去年岁尾与读者见面。

初版只印刷了500本,已送达徐州市相关研究部门、高校图书馆及考古专家。读者虽然小众,意义却是重大。本书主编之一,徐博党群部副主任陈钊很文艺地引用王勃《滕王阁序》,来说明他和李永乐主任共同编辑此书的目的:
“期望本书出版后,业界翘楚抑或跨界俊彦,借助此书之便利,井喷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可能是考古报告,可能是文保方案,可能是文物鉴赏,可能是诗词歌赋……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1953年是徐州现代考古的起点,至1985年的32年间,徐州史前考古和汉代考古成果斐然,然而相关资料由于印量少、纸质差,给后来者的接续研究造成困难。多方搜集而成的《徐州考古资料集成:1953-1985年》,为徐州考古大数据的建立走出了开拓性的第一步,也为徐州汉文化城市品牌的打造铺筑了坚实的研究基石。
■精彩导读
定格两千年的色彩 重启土层下的秘密
《徐州考古资料集成:1953-1985年》中收录的38篇汉代考古简报,为读者介绍了徐州早期汉代遗址和墓葬考古的丰硕成果,也展示了老一辈考古人的细致工作。
复活尘封的考古简报,为他人作嫁衣
与徐博众多考古博士为伍的陈钊是个特例。非考古、非文博专业的他,在2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参与过野外考古、藏品管理、文物普查、陈列布展及文化讲座等诸项工作。编印《徐州考古资料集成》在他看来,是目前的燃眉之需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陈钊在徐博2018年底动工的展陈提升改造工程中,参与布展提纲和展板的撰写,一连数月遍查馆藏和网络上有关徐州的考古资料。徐州地区早期遗址、墓葬的简报、调查散见于《考古学报》《考古通讯》《考古学集刊》《文物》等20多种刊物,是现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然而印数少,印刷质量也不好。想到考古研究者平时查找资料困难,他遂有了将之重新编排结集的想法。
“文博行业很多学术研究的基础在于考古报告、简报,然而考古调查、发掘简报通常分散于各类杂志中,一些常用资料往往被敏学者捷足先登,后来者不得而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在扫描录入资料方面,又因彼此间缺乏通气,造成重复劳动。”
《徐州考古资料集成》按文物年代共分四部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汉代、汉代至明代,59篇中汉代占了38篇。
用重新编排的方式“复活”简报,对于这种供专业学者使用的小众书籍来说,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技术难度,也增加了受质疑的可能性,无疑是一种自讨苦吃的做法。
尽管直接影印会省很多麻烦,但陈钊认为重新录入对使用者来说好处更多:“我们在录入中修改了多处原文笔误,对漫漶的图片、线图进行了重新修图,增补了256张高清图片,并在附录中增加‘关键词索引’,注明不可移动文物、被提及简报的名称、收录于原书的起始页码,本书的文图均可在论文中直接引用。”
发扬蚂蚁啃骨头精神,做细做实工作

自出版计划列入徐博科研资助项目后,徐博召集全馆专家对该书的受众、体例等展开研讨,陈钊负责图片的收集、处理,李永乐负责文字录入、校对,二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将工作一点点推进。
徐州地区早期遗址、墓葬的发掘单位不一,除了本地文博部门,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纺织科学院研究文物整理组、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苏北文管会、南京博物院等几十家单位,寻找收集这些考古资料,非一日之功。
陈钊说,是文物普查的积累给了他做这本书的底气:“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我的身份是摄影师、录入员、审核员、专家组成员。除了吸纳普查的资料,我们还在知网等线上搜索。图片更新是本书出版的重要意义,对于原书中模糊的图片,从27种出版物中替换了44张黑白图版,新增了48张线图摹写和123张彩色图片。”
“全书对同一文物的图片择优选用,对模糊的图片进行替换,部分新增彩照还采用了多图合一的形式,对所有原版照片、线图摹写均做了不同程度的修图处理,如断线补笔、残字重输、污渍擦除、降低灰度、去龟背纹、背景重置等工作。”
录入文字及校对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李永乐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如飞的录入指法为同事称道。李永乐说:“为方便更多的读者阅读,本书采用全简体编辑,在繁体字无对应简体字时,保留繁体字,不以造字的方式解决。”
原简报中有许多地名因区划变更与现在不同,对此,李永乐一一作了注释,并将原简报内容与现代有关资料加以比较,对不影响理解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遣词造句和异体字予以保留,勘正原文中少量笔误或印刷失误。
完善地方专题数据库,服务文化建设
在感谢了徐州博物馆新老领导、同事们的鼎力襄助之后,陈钊在后记中还幽默地感谢了Adobe Photoshop CS、CAJViewer 7.2、汉王PDF OCR、拖把更名器、朗读女语音朗读软件、搜狗输入法等程序员为这部集成的出版提供了技术力量。
他说:“早年杂志印刷水平比较差,在正文中只有少许的线图和分辨率在100以下的黑白照片,这次我们应用现代摄像技术和电脑修图技术,丰富了图片信息,这要得益于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本书的封面由徐州博物馆毕业于日本大学的艺术学硕士尹之博设计,主图为1956年出土于铜山洪楼东汉墓、现存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纺织乐舞画像石的局部。
选择这张图片做封面,诚然与洪楼汉画在中国汉代考古中的重要地位有关,但其中还有技术性“置入”。原来,陈钊与小他一旬的李永乐都属猴,为纪念二人的合作,陈钊特意选择了这幅屋顶上有两只猴子的汉画。
新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目前两位编者正在撰写总结论文,回顾汇编工作、归纳经验方法:李永乐的《一次“复活”考古简报的尝试》着重说明在这本书上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陈钊的《“复活”一本考古简报的流程》着重从技术的角度总结经验、分享技巧。
继往才能开来。据悉,徐州博物馆正在建设和完善以考古成果为基础的徐州汉文化专题数据库、徐州汉文化知识服务平台等,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促进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陈钊说:“作为徐博数据库系统工程,下一部考古资料集成的年代或可以至1995年,第三本至2005年,第四本至2015年,这样逐步将数据库完善起来,希望更多具有奉献精神的志同道合者可以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徐州唯一汉代彩色壁画“重现天日”

黄山垄出土的汉代彩色壁画摹本
徐州黄山垄汉代壁画墓是1958年冬天发现的,由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徐州市汉画像石保管组和徐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共同清理。据葛治功刊于1961年1期《文物参考资料》的文章,此墓在徐州东郊黄山垄村东南约一里处,当地人称“双孤堆”,墓内长10米、宽2.5米,分前、中、后,三室全部用大石条、板构筑,用石灰勾缝,在前室的四壁上皆有壁画,因年久和水浸的缘故,壁画大部分已脱落,只在西壁和南壁保存一部分。
西壁上层为车马出行图,下层为乐舞场面;南壁为墓门所在,门楣上画的也是车马出行图,门两旁各画—大人像,似是小吏或门卒。作者认为,壁画虽然多已残缺不全,但仍有研究、参考的价值,特别在江苏省是首次发现。
当年照相设备尚未普及,随文一起刊发的,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图片,壁画的真实面目已随该墓的后期破坏而不为所知。
所幸,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现任徐博陈列部主任的岳凯在书画仓库中发现了一块上世纪60年代江苏省文物联展的辅助展板,正是黄山垄发现的徐州地区唯一彩色画像石壁画摹本,展板说明中称壁画“笔道生动活泼瘦劲挺拔,色彩鲜明,极为美丽可爱”。
岳凯说,此画不知是哪位前辈所作,正是因为老先生的妙笔,让后人从彩色壁画摹本中欣赏到汉时生活和艺术创作的多姿多彩。
五十湅钢剑,汉代先进技术的见证
考古专家王恺1977年从西安调任家乡徐州博物馆,他在1979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徐州发现东汉建初二年五十湅钢剑》文章中说,1978年1月,徐州铜山县潘塘公社段山大队社员,在驼龙山南坡发现一座小型汉代砖室墓,经清理,在骨架左侧出土一把刻有错金铭文的建初二年五十湅钢剑。剑把正面有隶书错金铭文一行:“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孙剑□”二十一字。剑镡已残脱,铜质,内侧上阴刻隶书“直千五百”四字。
此剑身刃口及剑柄部分取样的鉴定结果是:组织由珠光体和铁素体组成,分层明显,各层含碳量不同,组织比较均匀,证明该剑是用含碳量较高的炒钢原料锻造而成。“湅”通“炼”,徐州出土的“五十湅”钢剑,反映了汉代的冶炼工艺水平。
自汉代开始,人们改变了以铜为主铸剑的历史,改用铁来铸造更锋利的剑,至西汉中期已知道通过增加剑坯锻打次数来挤出铁中夹杂物,这就是早期的“百炼钢”技术。在潘塘出土的这把剑,正是高级阶段的百炼钢成品、汉代先进冶炼技术的见证,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目前陈列在徐博的“金戈铁马”厅。
“明光宫”的奢华,一道未解之谜

“明光宫”的随葬品
在徐州博物馆“大汉气象”展厅,一组“明光宫”的鎏金器皿向人们展示了皇家的奢华。据王恺、李银德发表在1984年11期《文物》的《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1982年10月,徐州市石桥石灰厂在洞山采石时发现西汉墓一座(编为二号墓),“明光宫”的文物即在其中。
在这座墓的南边10米处有一较大石洞被编为一号墓,发现于1955年,石桥村许凤银雨后曾在该墓南约50米处捡得铜、玉器7件。考古人员对出土地点及整个洞山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些器物可能是一号墓被盗后的孑遗。
二号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67件,铜制品有鼎、锺、勺、灯、行灯、盘、釜、博山炉、镜、铃形器、刷、泡钉等,其中有10件刻有“明光宫”“明光宫赵姬锺”“赵姬沐盘”“王后家盘”字样。史载,明光宫建于太初四年(前101年),至始建国元年(公元8年)王莽“改明光宫为定安馆”,明光宫前后存世100余年。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城遗址进行钻探勘测时在城东部宣平门至清明门地段发现了明光宫遗址。
两位作者分析,一号墓规模之大,可与满城、九龙山墓相匹,墓主应为某代楚王;相距10米的二号墓或为王后墓,该墓“明光宫”铜器是首次出土。明光宫的宫廷用器如何出现在徐州?赵姬是谁?为何一号墓有玉衣残片,而二号墓没有?这些被埋藏的秘密,有待后世解答。
(来源:徐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