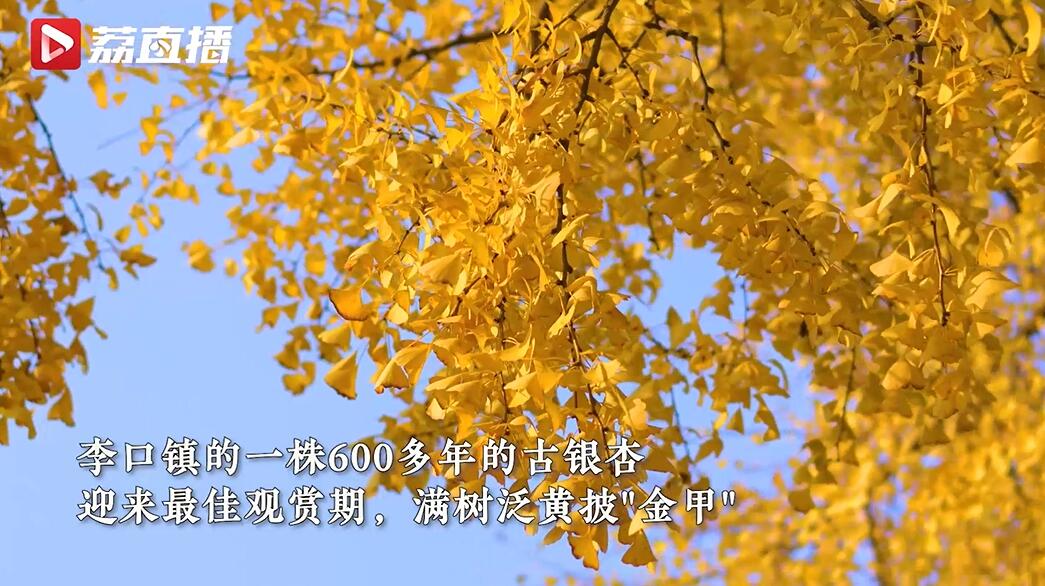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一部反映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生存状态的纪录电影《二十二》正式公映。
这部影片中记录了22名“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态,她们平均年龄超过90岁。她们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她们的生活看起来都如此相似:太阳出来,她们起床,吃饭,靠着墙根晒太阳。太阳下山,她们端着椅子回屋,吃饭,睡觉。平凡到,和我们自家奶奶的生活,不会有两样。
唯一的不同是,她们都背负着身心伤痛,剧烈到有的人终其一生无法直面。在我们看来乏善可陈的无聊日子,是她们用了自己的全部努力,才活下来、过下去的。
光影镜头下的老人令人动容,影片背后的现实更令人心痛。
2012年,“80后”导演郭柯完成了一部“慰安妇”幸存者短片的拍摄,当时国内“慰安妇”幸存者尚有32人,他因此把片名定为《三十二》。两年后,郭柯决定将所有“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都搬上银幕时,由于一些老人的离世,片名已经由《三十二》变为了《二十二》。
就在影片上映的前两天,8月12日,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离世,终年90岁。
随着黄有良的离世,从2014年至今,《二十二》记录的老人,仅剩8位。而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人。
郭柯将《三十二》和《二十二》两部影片的原版拷贝都捐赠给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他说,这是两部影片“最合适的归宿”。
爱笑的奶奶
前往桂林拍摄韦绍兰老人时,郭柯从不掩饰自己的初衷:猎奇。
2012年6月,郭柯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关于一个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和她日本儿子的故事。1944年,20岁的韦绍兰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3个月后艰难逃离慰安所。不久,她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儿子罗善学如今已70多岁,始终未能成家,还与母亲同住。他想结婚但没办法,谈了六个“妹子”都不成事,因为“妹子”的家人不允许她们嫁给日本人。
做了十多年副导演的郭柯有职业敏感,他看到故事的冲突,心想如果拍成片子一定很好看,“‘慰安妇’和她的混血儿子,两个人物身份都比较离奇,肯定有跌宕起伏的经历。”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记者,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二战期间中国有逾20万女性被强征沦为“慰安妇”。时至2012年,已知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32位,郭柯因此把片名定为《三十二》。
前往韦绍兰家之前,郭柯已经预设了情节,无非是网上搜来的悲惨和苦难,“不堪蹂躏”“血泪控诉”“求死不得”。
他准备了脚本和提纲,想要拍出大时代下被历史境遇改变的女人的命运。
出乎郭柯意料,韦绍兰日子过得清苦,每个月靠政府30元补助过日子,买得最多的是白菜,但她对生活乐观满足,“(钱)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怎么会够,怎么又会不够。”
韦绍兰爱笑,还爱唱歌,郭柯问她对将来怎么看,韦绍兰答:“这世界这么好,现在我都没想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要留得命来看。”
郭柯发现,只要不提那段经历,老人的生活都很好。
可他还是提了。按照惯性思维,“慰安妇”的纪录片必须挖一挖那段历史。
“当年日军把您抓走之后做了些什么?”问题一出,韦绍兰哭了。郭柯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继续追问,他想顺着眼泪拽出背后的记忆。
韦绍兰没有回答,转身走开。
郭柯突然感到沉甸甸的内疚,他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如果这是我奶奶,我还会这么问吗?”
在老人身后,郭柯也哭了,是“二三十年来都没有过”的大哭。“我确实觉得,当时我那副嘴脸,怎么能那样呢?就为了你要的那种表现力,这样去对一个老人,你这样能像个人吗?哪怕你拍出一个再牛的片子,奥斯卡、戛纳的获奖作品,你好意思吗?”
他当即调整拍摄计划,抛开脚本和提纲,把摄像机架在那里,以温和的方式记录老人的生活。
动人的平凡
苏智良教授和郭柯在拍摄《三十二》期间结识,他告诉郭柯,“慰安妇”幸存者的数量在快速减少,2014年已经从32位变成22位。
郭柯开始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不能再等了,来不及了。”他已经想好片名,就叫《二十二》。
然而投资依然没有着落。
他无奈发了朋友圈:“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来支持《二十二》的拍摄……”
演员张歆艺在这时候“雪中送炭”。她和郭柯在剧组有过合作,“我觉得他特别真诚,而且他想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有种和时间赛跑的感觉。”
张歆艺借给郭柯100万元,对他说,快去拍吧,不然老人就不在了。
有了拍摄韦绍兰的经验,《二十二》的基调早已定下。这一次,郭柯只想做忠实的记录者。
龙庆是郭柯的中学老师,也是郭柯纪录片团队的志愿者。她记得在《二十二》的拍摄中,自己有一次和老人聊天,老人讲起当年经历流下了眼泪,监视器后的郭柯马上喊停,“他对老人理解了。一旦触动到老人伤疤的时候,他不愿意让这种痛苦在老人身上再次发生。”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22位老人全部拍摄完毕。郭柯形容这22位老人的素材就像一座山一样,“要用100多分钟把20多个人全部讲明白,而且还要有情感传达在里面,我觉得好难啊。”他转而向台湾著名剪辑师廖庆松求助。
“不知道导演要干嘛”是廖庆松最初的观感,《二十二》太不像一部传统的纪录片了,没有解说,没有史料,没有故事线,“这样很难感动观众”。
郭柯不同意在片中加入历史画面,他觉得把“慰安妇”的资料和老人放在一起对她们是二次伤害,他告诉廖庆松:“我不一定要感动观众,我就想把老人们的真实生活展现给大家。”
廖庆松明白了郭柯的用意,“用一种饱含感情的眼睛去看,不是同情,而是充满关怀、爱惜的眼光,做人世间最后的凝视,希望这些老人在我的眼光中不会消失。”
郭柯内心里那个“说不清楚”的想法一下子被点破,“对啊,我就是要做这件事!”
上映就是胜利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但由于缺乏发行资金,只能在电影节和部分院线点映。
但郭柯仍相信,《二十二》是有机会的。众筹这个方式给了他启发。2016年10月,《二十二》在腾讯公益上众筹宣发费用,目标是100万人民币。
润智影业的总经理刘倩羽和硕果莲莲的创始人苏北淇参与了众筹活动,并决定为影片负责发行和宣传。众筹50多天后,资金停留在40多万。苏北淇判断,“这部分可能是从原来《三十二》的受众转化过来的,就卡在这个点上了。我们当时非常着急,因为你必须有钱,工作才能启动。”
直到12月,央视新闻频道对《二十二》进行了报道,出乎她意料的是,第二天100万众筹就凑齐了。留出20万的后期,最后宣发经费80万,是苏北淇经手过的最低成本的案子,“这仅相当于一部中等规模电影办一场首映发布会的钱。”
郭柯对票房没有很高追求,“能上映就是成功”。
“一个80后,有很多方式可以挣钱,也有很多方式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就执着于这件事情,挺辛苦的。”张歆艺评价。因此,借钱之时她就有准备,“纪录片怎么会挣钱?”
但她还是被影片质量所震惊:“这样的镜头,出现在贾樟柯或者王小帅的电影里都是非常好的画面,非常深刻,而且有技术含量。如果我是出品人,我会觉得他没有辜负我。”
她到现在仍在为影片吆喝,她主动给冯小刚写了信,她觉得仗义的冯导一定愿意帮她这个忙。随后,冯小刚在微博上进行了转发。紧接着,吴京、谢楠、何炅、李晨、舒淇等明星也都纷纷转发了冯小刚的这条微博。
这些天,《二十二》一直备受关注……
周末对话·
郭柯:
用平静和真实去对待她们
《周末》:为什么把纪录片捐赠给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郭柯: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是唯一经“慰安妇”幸存者亲自指认的、以“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念馆,是《三十二》《二十二》最合适的归属。纪录片在馆内播放,能让更多海内外人士了解“慰安妇”受害者的经历,推动“慰安妇”问题早日解决。
《周末》:你从2014年就开始带队拍摄《二十二》,一直到近日上映,中间这两年多的时间在做什么?
郭柯:从2014年7月份拍完到2015年8月份,一年多时间都在剪辑,主要是考虑以什么样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做了一年的后期,2015年10月份获得了公映许可证。可能是我的人脉不够广,找了一些发行的公司,他们也不愿意接这个片子。所以我就只能通过申报电影节,希望寻找一些出口,2016年基本上都在走电影节的事。2016年4月,我看到《鬼乡》这部电影,片尾有7.5万名韩国民众来帮助这个片子,我当时真的觉得看到一线生机。
到了年底,我走完了所有电影节的流程,当时正好有基金会的朋友找到我,说愿不愿意做众筹,其实是没有办法。
众筹推出以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发起方来监管这笔资金,不到2个月时间我们就筹齐了100万人民币,感谢这些网友,都特别热情,很多网友帮助了我们,名字也没留。32099人次,其实我的片尾才7000人左右,但大家看到都非常震撼,但是这只是一部分。
《周末》:说实话,片尾密密麻麻的众筹者的名单,确实让人非常触动。
郭柯:我自己每次看到这些名字时,情绪也会有很大波动。这些字幕都是我一个一个打上去的,我也真心感谢每一个人,只要给我发过邮件的人,我都会记下他的名字,一个一个打上去,我害怕疏漏一个人,所以这个必须我自己亲自来。
《周末》:你自己怎么评价《二十二》?
郭柯:其实我们没有人愿意去面对痛苦,包括我都选择不看老人们受害的文字记录。我们怎么去记住这段历史,角度很重要。看了以后大家会知道《二十二》是一部非常平静的片子,我希望用一种更加平静和真实的方式,让大家先能接受这些老人、喜欢这些老人。如果我一上来就说她们是受了迫害的,大家要去关注,我觉得这种方式略显生硬,应该用更加温柔的方式让观众与她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