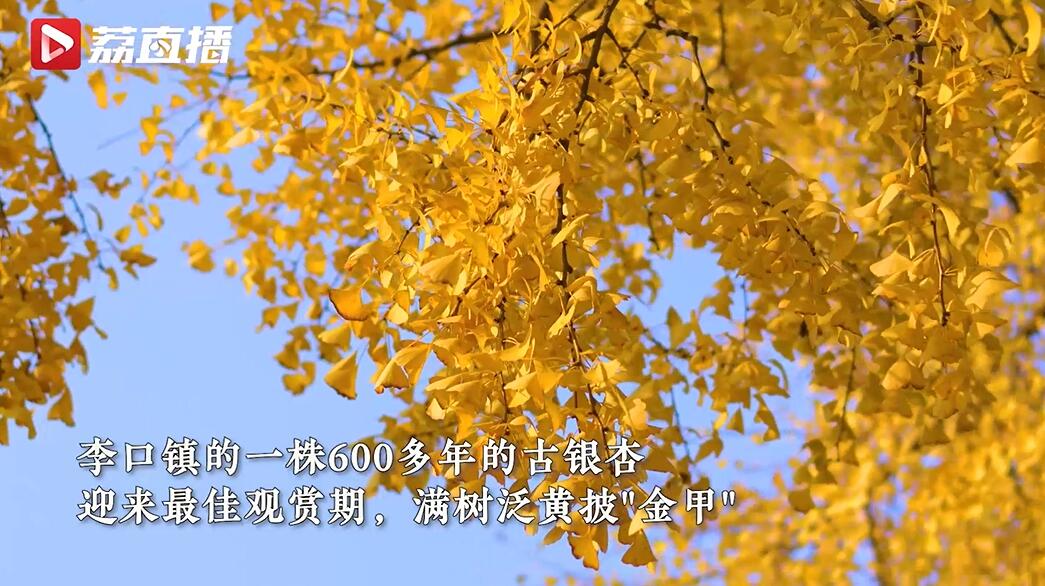2000 年,毕飞宇 36 岁,刚写完《玉米》。李敬泽也 36 岁,刚出版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毕飞宇断断续续地看李敬泽的这本书。然后,这本书被一个法国老头带到法国去了,不知所踪。2017 年,这本书以《青鸟故事集》的名字增补再版,而且还出了法文版。毕飞宇认为这印证了李敬泽说的一句话——物比人走得远。
元旦期间,李敬泽来南京吆喝这本书,并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三天假期。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原《人民文学》主编。著有《颜色的名字》《为文学申辩》《反游记》《小春秋》《致理想读者》等。
在南京跨年
读了一首余光中的诗
12 月 31 日下午 4 点整,李敬泽准时出现在约定的采访地点。打车来的,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随行,轻车简从得让人忽略他的"副部级"身份。
年初就说要来南京,可一直拖到年尾。一来是给自己的新书《青鸟故事集》吆喝,"再不吆喝,对不起人家出版社";二是参加 31 日晚上先锋书店的跨年诗会。
听说这个诗会比春晚的时间还要长,40 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轮番上场诵读,一直进行到元旦早上。欧阳江河、舒婷这些诗歌界的大神也都出动了。李敬泽虽然不写诗,但他愿意来凑一凑热闹。
他请作协的诗歌研究专家为他挑首诗,"要适合在南京读,适合过节读",最后挑了余光中的一首《大江东去》。挺合他心意。
"余光中南京人嘛,我朗诵他的诗肯定可以,他们那些诗人肯定没选,诗人肯定得选啥啥耶娃、啥啥列夫,这样方显高大上。"当别人都奔着"高大上"而去时,自己选择"接地气",其实这也是他的一种策略。
又听说自己和欧阳江河分在一个单元,李敬泽更自信了——"那不要紧。怎么我也得比老欧阳强!他那个四川口音。"
烤鸭有钱就可以吃
敬泽岂是有空就能见的
李敬泽的第一身份是批评家,但他并非那种以批评为志业的人,"我压根就没有想当批评家,三十岁之前没写作批评文章。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理想还是做一个无所事事的读者,而不是读一本书就要想着怎么写批评文章。"
很大程度上,他的批评生涯是和编辑生涯相伴而生的。1984 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进入《小说月刊》当编辑,六年后调到《人民文学》,仍然是做编辑,直到 2008 年升任这本文学"国刊"的主编。身处中国文学中心性的现场,一干就是三十年。
在文学界,特别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看来,李敬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和他们同样年轻的李敬泽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把《人民文学》办成了实验小说的大本营之一。他的专业、严苛,以及特有的亲和力,让人印象深刻。而 2000 年以后崛起的阿乙、冯唐、梁鸿、李娟这些人,则属于他在编辑生涯末期发掘的新人。
对于更多的写作者来说,李敬泽更显著的特点是"不骂人"。毕飞宇说,李敬泽拥有无与伦比的亲和力,对年轻的作者尤其是这样,"他总是鼓励、再鼓励,他的领袖气质是天生的。"
有个段子因此而流传一时,那就是——"文艺青年到北京三件事:吃烤鸭、爬长城、见敬泽。"
不过现在,烤鸭有钱就可以吃,敬泽岂是有空就能见的?
"这真是老段子了,十几年前大概还沾点边儿。现在我哪有那么多工夫见人啊,再说我现在也不做编辑工作。现在年纪渐长,到晚上只愿在家呆着看看书、写写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整天在外头吃饭会朋友。"
2012 年,李敬泽卸任《人民文学》主编,转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没多久,又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脱离了一线文学现场的李敬泽,强调自己现在是"前批评家"。"我可能还会做一些和批评相关的工作,但是就我个人的旨趣和兴致来说,我大概不会再去把批评作为我写作的主要方向。文学批评作为一项志业或者一个写作方向,对我来说,这个基本 over 了。"
"作家教父"做烦了
要当"新锐作家"
批评家不批评了,那干什么?进行"更宽泛意义上的写作"。
和李敬泽相交二十多年的毕飞宇说:"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有极高的写作能力。我一直劝他写作,可他不以为然。许多批评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手上拿了一个手电,照亮了别人,唯独看不见自己,敬泽年纪也不小了,他在这个时候拿起笔来,令我无限欣慰,虽然有点晚,但是也不晚。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2017 年一个‘新锐作家’横空出世。"
2000 年,毕飞宇 36 岁,刚写完《玉米》。李敬泽也 36 岁,刚出版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毕飞宇断断续续地看李敬泽的这本书。然后,这本书被一个法国老头带到法国去了,不知所踪。2017 年,这本书以《青鸟故事集》的名字增补再版,而且还出了法文版。毕飞宇认为这印证了李敬泽说的一句话——物比人走得远。
时隔十几年,增补再版的这本书所引发的热度,让李敬泽感到意外。
书中的主角都是一些在遥远的旧时光,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和东方的异族人,他们或是肩负传播信仰使命的西方传教士,或是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波斯商人,或是一些狂热的异域文化的爱好者与崇拜者。
在 2000 年以前,书中描写的这些中国文化和异国文化的遭遇,以及这些遭遇中所发生的偏僻的故事,基本上是一个冷到冰点之下的知识点。十几年后,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和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几乎成了一大热门。
"我在十几年前写这些故事更享受。如同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做着不为人知的事儿,从中得到一种怪异的乐趣。"
"我觉得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
他喜欢举一个例子——明朝嘉靖年间,红薯传入中国,相比于这件事,嘉靖皇帝算什么呀,张居正都没有那么重要,这件事才真正对中国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嘉靖年间,中国的人口六千多万,过了一百多年,变成了四亿。塑造中国的就是那些种红薯的无名者。
"新锐作家"李敬泽在 2017 年有点锐不可挡的意思。在另一本书《咏而归》里,他回溯中国精神之上游,讲述春秋年间的事。用评论家何平的话说,这些久远的发生在历史幽暗角落里的故事,终于等来了一个理想的作者。
小说家们更为关心的是,李敬泽会不会写小说。他的《青鸟故事集》,有人说是一本历史随笔,有人说是一本"微历史",也有人把它看成一本现实与想象混搭的小说集。12 月 30 日,在先锋书店的读者见面会上,小说家鲁敏又问了他这个问题。对此,李敬泽采取了一种"战略模糊",不说写也不说一定不写,"不把话说死"。
生活是一件值得好好对待和认真过的事情
作为文学圈的时尚 ICON,李敬泽是出了名的穿衣讲究。棕色皮夹克搭配深褐色围巾,胸前一枚长约 5 公分的玉饰画龙点睛。
"这是个玉勒子,西周的礼器。西周的挂饰通常很大,由珠子、玉件串成很大很复杂的一挂,这个勒子是其中的一个部件。"他有两三个勒子,换着戴,搭配不同的衣服。"像这个呢,比较大,沁比较重,适合冬天戴在毛衣外面。夏天会戴一个白玉的。"
"衣服是我在小店淘的。我给你报个价吧,基本没有超过两千块钱的。身上这件皮衣正好赶上打折,西班牙的一个牌子,三千块钱。不贵吧。"平时在北京难有闲心逛街,出差到上海广州乃至小县城,有时间就逛街,而且一定要一家接着一家仔细地逛,"漏过一家就心有不安,所以宁可一个人逛,免得把别人搞崩溃。"
当然围巾比较贵。两端参差地垂下来,按照毕飞宇的说法,"校正过左右的比例关系"。脖子上的围巾,现在已然成了他的标志了,哪天出门不戴围巾,别人看着都不习惯。所以,还是要讲究点品质。
面对八卦盘问,李敬泽不疾不徐、有一说一。说完这些,他也忍不住笑,"好像俩女人在谈,是吧。"
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敬"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别根本的精髓是‘敬’,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价值都是从‘敬’升华出来的。但这个被咱们玩丢了,让日本学过去了。"
"生活是一件值得好好对待和认真过的事情,对生活要怀着热情和敬意。每天要穿什么衣服,还是会过一下脑子。"
由这个引申开来,"敬"不仅是出门前要临镜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对人事有敬意,要"临事而敬"。
同为老兔子、摩羯座,毕飞宇认为对李敬泽相当了解,"他走到哪儿都慢声慢语的,给人感觉不太认真,其实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非常摩羯座。我俩都属于这种人。"
这种认真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审美,体现在毕飞宇身上,就是热衷健身,对完美体型孜孜以求;之于李敬泽,则是穿衣要得体、讲究。
喝酒,现在大家都较量不动了!
在南京,不免谈起江苏的朋友。
"我跟江苏几拨儿作家都很熟,现在还活跃的老一些的赵本夫、范小青、周梅森、储福金,再年轻点的苏童、毕飞宇、叶弥、荆歌、鲁敏 …… 都没法列举,说实话,你能报出名儿来的,差不多我都熟。"
" 90 年代中期,江苏有一批比较年轻的作家,包括当时韩东、朱文周围的一批作家,其中很多现在不写了,但我跟他们也都有很密切的交往。"想起我的一位同事也曾是这波儿"年轻作家"之一,也早就不写了,但李敬泽点点头:他写小说,也写诗。看来故人他都记得。
"我跟你们江苏作家的交往,主要体现在年轻时候喝酒上的较量。当然现在不行了,现在大家都较量不动了。"
李敬泽在文学圈酒名赫赫,但他的酒量,一直是个谜。
储福金估计,年轻时候的李,两斤酒应该不在话下。十几年前去北京开会,范小青几个人撺掇着找李敬泽喝酒,他们认为储福金也能喝,就想让这俩人拼一拼,他们在一旁看好戏。他俩偏不中招,互相之间不喝,不停地跟别人喝,结果想看戏的一帮人喝得大醉。
"过去特别能喝"的周梅森说,"还是他(李敬泽)能喝"。
毕飞宇和李敬泽喝过太多回,但不清楚李的酒量,因为没见他醉过一次,"我没有资格跟他谈喝酒,在敬泽面前谈酒,我就是个笑话,他的酒量是我的四到五倍,但每次都不是我把他扶回去,都是他把我扶回去。"他打趣说,"敬泽不仅才华横溢,酒量卓著,还心地善良。大概十多年前,我去北京领奖,酒后他把我扶回房间,见我吐了,因为怕我出事,一直守到了下半夜,最后对我说:没事啦,那我走啦。说起这件事情就非常感谢。"
不过,这些都作江湖笑谈了。"现在哪里还能喝大酒啊?"李敬泽说,现在的他,一个星期也不出去一趟,"谁要是给我打电话,我首先会警觉起来,问是不是晚上要吃饭"。
接着,他又感慨,"当年我们是比较能喝,战斗力比较强。江苏作家还是老一代的储福金、周梅森他们能喝,年轻这一代不行。"
李敬泽是元旦晚上走的,在南京的几天,他没惊动太多朋友。"没聚。来也不招呼,走也不招呼,悄没声的我就走了,顶多他们回头看到朋友圈,看到你们现代快报的报道来讨伐我。"
其实,元旦那天是毕飞宇陪他过的,中午吃了个便饭,没喝酒,喝了茶,又在宾馆聊了一下午的文学,"他聊他的写作,我聊我的写作。"毕飞宇说。
对话
批评家写小说常常写成丑闻,可还是忍不住
没有想象,无法抵达历史的真实
读品:《青鸟故事集》出版后,很多人分不清它的体裁界定,既是散文,也是历史随笔,也像是一部充满了想象力的小说。
李敬泽:我确实有意识地给自己自由。其实我们先秦时代的文章,并不太受体裁文体的限制,你说庄子写的是什么呢?你要说庄子是个散文家也怪怪的。很严肃的史书《左传》《史记》都有大量的小说笔法,好多纯属想象,也有很多人挑过毛病。有他们撑腰,我也就不用那么在意这些问题。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你必须求真,但求真中包含着想象。完全不靠想象,就无法抵达过去。
读品:真的有历史吗?或者历史只是一种想象?
李敬泽:我们在谈历史的时候,往往会谈到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认为历史的真实的价值是第一位的,但是历史的讲述中,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的价值——想象力。我们怎么讲述历史,涉及到我们怎么想象自身。客观、绝对真实,这在历史叙述中是做不到的,只要你写,都必然带有主观性,同时也就带有了你的视野。
比如我们现在讲丝绸之路,那是汉代以后持续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你如果看"二十四史",并不能看到多少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述,为什么?因为这件事不在当时那些史家的想象、认识范围之内,这就需要我们眼光重新调整。有很多很多历史是被我们遮蔽的、遗忘的,仅仅作为死的史料放在那里,没有被我们纳入到历史拼图中来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本身就饱含着想象,包含着怎么去看它的这种眼光和视野的变化、调整。伟大的历史学家,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叙事者。如何讲述,这在历史中从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
读品:你会去写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吗?
李敬泽:批评家写小说经常写成丑闻,可还是忍不住。在这个问题上,我要保持一个"战略模糊"状态,不把话说死。应该说,纯粹的小说对每个批评家都构成一个诱惑。不要说批评家了,不都那样吗?我那天还听郭德纲说呢,很多相声观众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也能上去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问题是,都忍不住啊。批评家写小说真不是件明智的事,是很冒险的一件事。当然永远有例外。也没一个规律说批评家一定写不好小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例外。所以丑闻也就由此而来。
批评的同时一定有所捍卫
读品:这本书很多人点赞,似乎没有人敢挑你的毛病。
李敬泽:做批评那么多年,我还不至于听不出来别人是真夸还是客气。老大不小了,哪能都指着那几句好话?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说法,对我来说也还是有教益。对一个作品的阐释,溢出了作者的意图,这是很正常的。
我也不至于是一个不懂事的老糊涂。在我写得很差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把它印成书。如果真的不好看、真的没力气了,就别写了,那时候我就会去跳广场舞了,我觉得那是真正值得做的事儿。
读品:在做批评家的时候,你也很少"批评"别人。
李敬泽:当你批评的同时,一定有所捍卫和坚守。任何批评家,包括带有一定进攻性的批评家,必定是带着捍卫和持守,为好的价值开辟空间。批评一定包含着正面的价值,包含着对一个时代价值的引领。
读品:身为文学界最有话语权的批评家,这是什么体验?
李敬泽:我没认为我有什么话语权。无非是批评工作,和在文学生活中作为一个参与者、组织者,我的工作做得比较多,大家听到你声音的机会比较多,如此而已。如果这确实是个话语权的话,那你确实要审慎和尽可能准确地使用这个话语权。话说回来了,我现在是个"前批评家"。
文学不是种庄稼,今年长了明年也会长
读品:说起江苏文学,都觉得前辈作家们很厉害,但现在似乎面临着断档的问题。
李敬泽:文学不是种庄稼,种庄稼今年长、明年不长很焦虑。文学这片地,不一定今年不长、明年就一定能长,但也许大后年忽然就冒出来。换句话说,急又有什么用呢?它就不长,你能怎么办呢?
读品:苏童、毕飞宇他们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重要作品。
李敬泽:很多才华都是适逢其时的,才华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不像春天来了草就长出来了,有时候有很多机缘。你别忘了,苏童、毕飞宇他们正好是赶上了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变革。每当文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忽然一大群人就冒出来了。现代文学那批人很厉害、很伟大,也是因为他们正好赶上了新文学革命,整个范式发生了改变,一大批人应运而生。与其我们去思考长不长庄稼的问题,不如去思考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个巨大的变革的可能性。
读品:有没有你比较关注的 80 后、90 后作家。
李敬泽:你还是在焦虑这个问题。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二十多岁出名那是时代的特殊现象。对一个作家来说,40 岁上手,50 岁写出扛鼎之作,小说家是需要老妖精,老妖精是需要熬的,千年的狐狸需要岁月的熬。
就拿苏童、毕飞宇来说,安知他们已经写出他们一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作品了?他们也就 50 出头吧,还没到德高望重、竖起铜像的时候吧?不是说他们谁得了茅奖了就可以把他们供起来了,我觉得离供起来都还远着呢。我们依然还可以对他们满怀期待,包括我们熟悉的像叶弥、荆歌、鲁敏这样的作家。
这两天都在晒十八,我还懵呢,怎么就突然晒十八了。告诉我说是因为 00 后十八了,那你可以想见,再过两年,我们就得为 00 后出不出大作家而焦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