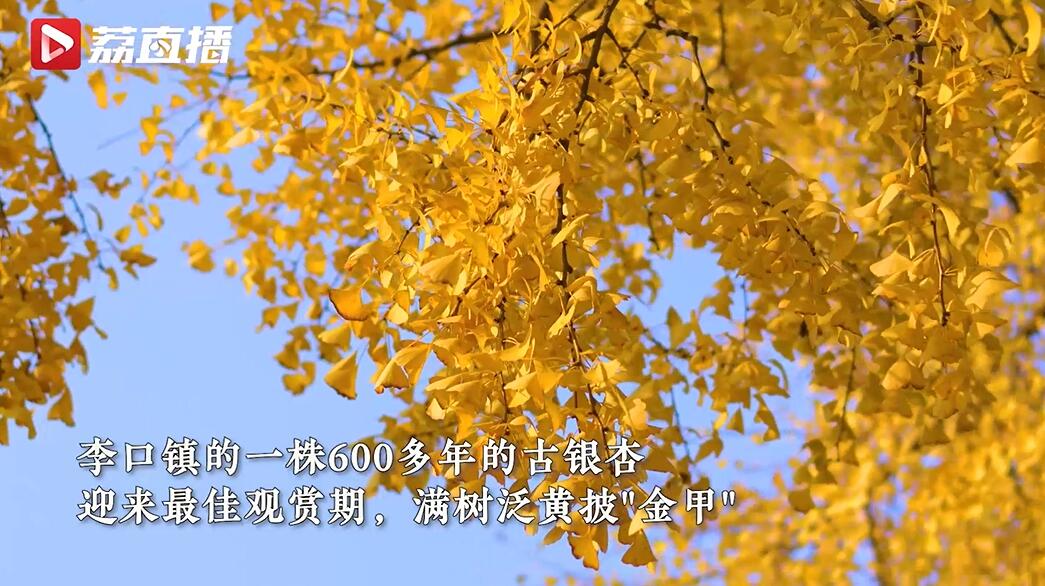编者按:近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2017)获奖名单揭晓,文学苏军再创佳绩,朱辉、胡弦、王尧三人分别摘得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文学理论评论奖。我苏网对三位获奖者分别进行了专访。以下是对文学理论评论奖获得者王尧的采访。
王尧,文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和《收获》发表专栏文章。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研成果曾获省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评论家奖等。2018年凭借《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 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小苏:我们就从这次获奖的文章说起吧,你研究的是汪曾祺,是不是因为对汪曾祺有特别的关注或者喜爱呢?
王尧:关于汪曾祺的研究,是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当代作家研究系列之一。近几年我比较强调文学史的关联性研究,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为参照,讨论作家作品。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在人性的呈现、语言、文体等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汪曾祺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人格特质和生活方式对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如何创新阐释汪曾祺何以成为汪曾祺、是我重读的重点。

小苏:你是怎么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的?
王尧: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文学的人,在乡下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我仍然能够从村庄的老师或兄长那里偷偷借到文学书籍,然后在油灯下阅读。我在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叙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史。上大学前发表过所谓散文诗。带着作家梦进了大学中文系。在大学受到学术训练,然后读学位,文学研究成了职业。我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研究文学史,再做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之余,写作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读书》开个专栏,出版了多种散文集,曾经获得紫金山文学奖之散文奖。今年又在《收获》杂志开设了散文专栏“沧海文心”。
小苏:你曾经说过,虽然自己在大学工作,却花了很多时间在作协。那么,你是不是跟作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你的研究有影响吗?
王尧:大学里有作家,作协里有学者,虽然体制不同,但实质性的边界是没有的。苏州大学和作协系统一直有密切的关系。我的导师范培松教授也曾经在作协兼职。现在的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曾经是我们中文系的老师,也给我上过课。当代文学批评因为研究同时代的作家,不可避免会和一些作家熟悉。我主持过“小说家讲坛”,主编过“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等。和作家的熟悉程度不影响批评家对作品做出独立的判断。我曾经说过,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关系建立在文学信仰基础上。

小苏: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特别快,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异常丰富,游戏、影视剧等占用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你觉得现代人还有必要读文学吗?文学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王尧:我从来不认为文学会死亡。只要人类有精神生活、审美生活,文学就有不可动摇的位置。当然,人的精神生活、审美生活是多样的,因而会有不同的选择。我尊重多样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读者,但我鼓励读者阅读经典。人需要娱乐,但不能娱乐至死。
小苏:批评家从事的是研究工作,相对来说比较专业。那么,你认为批评家在文学活动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尤其是对于普通文学爱好者来说。
王尧: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独立的创造性工作,应当不受非文学、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这根链条上,批评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他要通过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对现象的透视,做出价值判断,引导读者。现在的问题是,文学批评常常局限在专业范围。媒体应当建立一种沟通的平台,我期待媒体在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引导读者。过去曾经有一些读书类的节目、栏目做得挺好的,但现在似乎越来越少了。
小苏:有哪些作家、作品对你影响比较大吗?你有没有偏爱的作家?
王尧:这需要开出一长串名字。身体里流淌的是文学的血液,会和许多作家作品相遇。如果说有所偏爱的话,鲁迅是其中一位。
(我苏网记者/土土绒)